本文作者:heymax
隻是因為拉肚子,就住進瞭 ICU,還住瞭 28 天?
7 月的一個下午,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僅剩的一張空床上就轉入瞭這樣一個中年男人。病房裡,他下身裹著兩層尿不濕,身上插滿管子:呼吸機導管、中心靜脈導管、有創動脈壓檢測管、胃管、腿部的 CRRT(連續腎臟替代治療)置管......

科室內救治場景,圖源:作者提供
協助轉院的當地醫生表示,患者已經連續腹瀉瞭 20 多天:「患者在 5 天前住進瞭我們醫院,當時入院診斷為『感染性腹瀉』。」
「一直找不到感染源,隻能常規抗感染。治療過程中,患者的病情急轉直下、出現少尿和呼吸困難,發展成瞭現在的膿毒性休克。有創呼吸機和 CRRT 都用上瞭還是沒好轉。」
當地醫院與傢屬商議後,將患者轉院尋求進一步治療。
免疫抑制,怎麼抗感染?
轉入華西重癥醫學科之後,患者的初步檢查結果並不樂觀:體溫 38.4°C,脈搏 130 次/分,肺部聽診聞及少量濕囉音,呼吸機吸氧濃度 80%,中心靜脈導管快速的泵著去甲腎上腺素(0.4ug/kg/min)。
傢屬十分著急:「他這 10 多天來,每天起碼腹瀉十多次,都是深綠色的。」
重癥醫學科的醫療組隨機發現這位患者並不是第一次來華西,病歷系統顯示:患者 55 歲,2 年前因肝細胞癌合並肝硬化在本院行肝移植。術後使用他克莫司(2 片 bid)、嗎替麥考酚酯(3 片 bid)、西羅莫司(1 片 qd)等藥物控制排斥反應,兩年來按時復查、病情穩定。
肝移植術後患者出現感染,並不是什麼小事。
下級醫院在進行抗感染的同時,還停掉瞭他的所有免疫抑制藥物,這讓治療組有些意外:像這樣因肝癌接受肝移植的患者,在《中國肝癌肝移植臨床實踐指南(2021 版)》中,雖然對於如何維持患者免疫平衡狀態尚無統一的臨床方案,但並不主張免疫抑制劑的全線撤除。

肝癌患者肝移植後的免疫抑制,圖源:《中國肝癌肝移植臨床實踐指南》
患者轉入後的第一道難題由此產生:患者腹瀉的感染源一直不明,現又繼發嚴重感染,而外院的抗生素方案已經級別很高瞭,加上免疫抑制劑還被停掉瞭近一周,初步治療方案如何制定?
「雖然指南不建議全線撤除免疫制劑,但患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多天的腹瀉導致血液濃縮,免疫抑制藥物濃度明顯上升。」重癥醫學科張中偉教授表示:「患者住院時他克莫司血藥濃度已較前升高瞭數倍,結合患者血常規中極低的淋巴細胞水平,現仍處於過免疫抑制狀態。」
同時,患者廣泛的感染和多臟器功能損害也讓血壓維持起來舉步維艱。如果再使用免疫抑制藥物,患者感染的范圍和程度再加重,便可能是壓上瞭最後一根稻草。

病情討論,圖源:作者提供
討論後,治療組組長一錘定音:「目前暫時延續外院停用免疫抑制劑的處理,後續密切觀察血藥濃度,待免疫功能恢復後再繼續使用。」
初步治療方案就這樣被敲定:停用免疫抑制劑,針對已明確的肺部及腹腔感染進行抗感染治療(亞胺培南西司他丁 1g q8h,伏立康唑 0.2g q12h),與此同時,也要重點追溯導致患者腹瀉的「元兇」。
患者的感染類型,在檢查後初步有瞭方向:患者入院當天的糞便常規並未報告可能的病原學,但第 2 天的血培養結果顯示 G+ 球菌感染;血液檢查、胸部 CT 則提示同時存在真菌感染。拿到結果後,患者的抗感染治療中增加瞭兩性黴素 B(10mg bid)和替加環素(100mg q12h)。

監護室內,圖源:作者提供
在這樣的治療下,患者的病情逐漸好轉。入院第 3 天時,腹瀉就已經止住;到瞭第 5 天,患者的體溫高峰逐漸降低,氧合指數上升至 300 左右。
隨著鎮痛鎮靜藥物的減少,患者拔除呼吸機、轉至普通病房指日可待。治療過程中,患者的淋巴細胞計數持續上升,提示免疫功能也有所恢復。但此時抗感染仍是重頭戲,於是治療組按照此前制定的方案,恢復瞭嗎替麥考酚酯(500mg bid)的使用、抑制免疫功能。
目前為止,病情似乎盡在掌控之中:腹瀉止住瞭,各項指標也變得平穩。傢屬十分開心,治療療組在欣喜之餘卻暗暗隱憂:感染的原因一直沒有明確。不從源頭上解決問題,隨時有病情反復的風險。
血液中全是蟲子
第 7 天,患者突然出現大量水樣腹瀉,多層尿不濕都難以阻擋。血壓不穩,氧合指數下降至 200,各項炎癥指標上升。而當天患者出現瞭異常的肝功能指標,提示藥物性肝損傷的可能性。
迅速惡化的病情讓治療組措手不及,立即停瞭腸內營養,加用止瀉(黃連素)和保肝藥物(多烯磷脂酰膽堿 + 異甘草酸鎂),並調整抗生素方案(頭孢他啶阿維巴坦 2.5g q12h,氨曲南 1000mg q8h,伏立康唑 0.1g q12h,硫酸粘菌素 75 萬 u q12h)。

圖源:作者提供
治療又回到瞭原點:必須得找出腹瀉的原因。在此前檢查的基礎上,大傢有瞭新的方向:既然糞便常規無法明確導致腹瀉的病原體,患者又是接受免疫抑制劑的特殊人群,那麼病原體有可能不典型,也可能為寄生蟲感染。不如直接看看患者的胃腸道、一探究竟。
在這樣的猜想下,患者第 8 天進行瞭胃腸鏡檢查,通過腸鏡下看到的情況令人震驚:盲腸部及升結腸節段性粘膜改變,可疑特殊感染;節段性改變也讓大傢眼前一亮:這說不定就是問題的源頭。
緊接著,血液標本的高通量測序(NGS)顯示:患者的血液中存在大量隱孢子蟲的基因片段。實驗醫學科對糞便的改良抗酸染色結果也指向瞭同一種結果:隱孢子蟲。

該患者的胃腸鏡檢查結果(左),改良抗酸染色結果(右)
診斷總算明確:隱孢子蟲感染。
隱孢子蟲是一種體積微小的球蟲類寄生蟲,正常人常因不潔飲食、遊泳時吞咽水、觸摸寵物後未註意手衛生等感染,主要表現為急性胃腸炎癥狀:排帶黏液的水樣便,有的伴有明顯腹痛,尚有惡心、嘔吐、低熱及厭食;但病程為自限性,數周即可自行痊愈。[1-4]
對於像患者這樣進行過器官移植的人群,隱孢子蟲卻極有可能致命。慢性的水樣瀉難以控制,病程可長達數月,並伴有嘔吐、上腹痙攣、體重減輕等癥狀。近年來,隨著器官移植手術的增多,隱孢子蟲成為瞭危及接受器官移植患者生命的重要病原體。[5,6]
在與患者傢屬共同回溯患者相關的生活史時發現,患者在開始腹瀉的那天,曾因嘴饞、在街邊買瞭小吃。
病因終於明確,治療卻重新陷入瞭困境:當前的治療方案需要更改,新的醫囑怎麼下?
在此前的治療相關案例中,通常為原發性免疫缺陷的兒童或腎移植患者,肝移植術後感染患者十分少見,更沒有相關指南可以參考。
唯一可以用的藥,國內卻沒有獲批
沒有指南的情況之下,整個醫療組開始查閱起瞭近年來學界所有已發表、可供參考的個案報道,最終發現一例被診斷為「隱孢子蟲感染」後、經治療徹底痊愈的 CD40L 缺陷的嬰兒。而該患兒的治療方案為:阿奇黴素 + 硝唑尼特(NTZ)。[7]

治療參考案例及案例的治療過程,圖源:參考文獻 7
報告中的 NTZ 讓大傢眼前一亮,立刻找出這個藥的使用說明,肝移植患者不比普通患者,用藥禁忌更多。但藥物說明像一盆涼水潑在瞭每個人臉上:NTZ 是全球唯一被批準的抗隱孢子蟲藥物,但國內並未獲批;並且對於免疫缺陷人群,也並不推薦使用。
NTZ 主要通過抑制丙酮酸鹽,鐵氧化還原蛋白氧化還原酶的酶依賴性電子轉移反應來對隱孢子蟲主要起到抑制作用。但免疫缺陷的人群並不適合:它需要通過人體正常免疫系統的放大作用來清除隱孢子蟲。[8,9]
NTZ 暫時被放棄,但這個案例也提示瞭「阿奇黴素」的有效性。於是,醫療組決定先據此進行一些嘗試:口服阿奇黴素(1000 mg tid)+大蒜素(500 mg tid)來抗隱孢子蟲。
之後 5 天,患者腹瀉略有改善,但肝腎功能卻繼續惡化,持續 CRRT 治療再度被啟用。到瞭第 18 天,患者的谷氨酰轉肽酶及堿性磷酸酶持續升高,提示患者出現瞭隱孢子蟲逆行膽道感染,此前抗隱孢子蟲感染方案宣告失敗。
在此時,NTZ,成瞭唯一有可能止住腹瀉和擋住隱孢子蟲繁衍的藥物。
患者的子女建議:從海外寄回 NTZ 進行嘗試。醫療組再次研究起瞭 NTZ 的說明書。

病情討論現場,圖源:作者提供
對於其中提及的「不推薦在免疫缺陷的人群中使用」,大傢有瞭新的理解:這一條是基於其不具備正常的免疫功能提出。但本次的患者卻較為特殊:他是人為幹預所致的免疫缺陷、即免疫功能是可逆的。張主任最終決定:「將他的免疫相關指標提起來、恢復一定的免疫功能之後嘗試使用 NTZ。」
向海關報備後,患者的子女很快從海外郵寄回瞭 NTZ。而基於患者之前的治療經驗以及文獻參考,抗隱孢子蟲方案更換為硝唑尼特 500mg tid 和大蒜素 500mg tid 口服;與此同時,使用環孢素進行免疫功能抑制、將 CD4+ T 細胞控制在 100~300/mm3,以達到清除隱孢子蟲的目的。
方案施行 2 天後,患者的腹瀉次數逐漸減少,所有人都松瞭一口氣。隨著肝腎功能逐漸恢復,患者在進入 ICU 的第 22 天,終於停用瞭 CRRT,並在次日順利脫離瞭呼吸機。在第 24 和第 25 天,患者兩次的糞便抗酸染色中均未找到隱孢子蟲,宣告著治療的最終成功。
入院第 28 天,患者終於渡過危險、轉入瞭普通病房。

致謝:本文經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副教授 何敏 專業審核
策劃:sysoon|監制:carollero、gyou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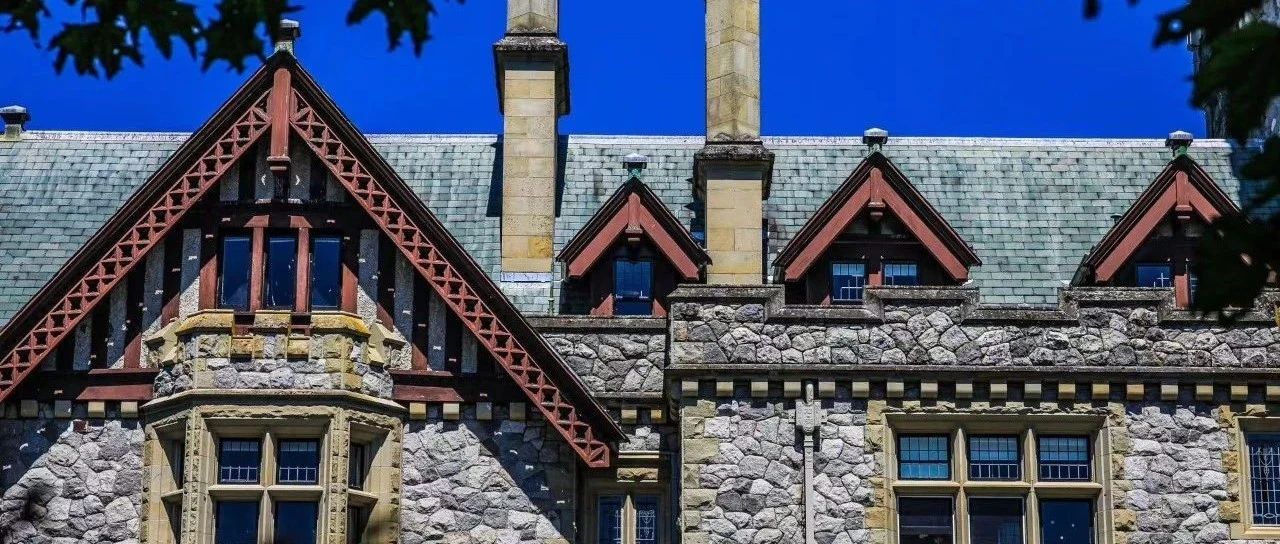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