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中國城市,年輕人最向往?
數據顯示,2022年常駐人口增長最多的10個城市,分別是長沙、杭州、合肥、西安、貴陽、南昌、昆明、武漢、鄭州和青島,均非一線城市。從人才流動的趨勢來看,重慶、成都、杭州等新一線城市已逐漸成為北上廣深不可小覷的對手。
吸引年輕人跨城流動的,不隻是工作機會。大城市擁有的文化生活——豐富的文藝活動、活躍的社區文化、熱鬧的公共生活,是很多年輕人留戀一線城市的重要原因。如今,非一線城市也在經歷一場“文藝復興”,文藝活動的質量甚至反超瞭部分一線城市:
文藝展覽層出不窮,免費的文化沙龍夜夜不斷,年輕人擠在書店、咖啡店、酒吧、老社區民房的狹小空間,或在戶外的茶館、廣場、草地,圍觀和參與一場又一場文化對話。
一些返鄉和退隱的京滬青年,把一線城市的公共生活帶回到這裡來。但這些曾經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城市,本身就具有一種內在的文藝力量。新周刊專題“城市之光”將深入這些城市的內部,觀察這場“文藝復興”何以發生、何以持續。
從書店開始,重返公共生活
5月中旬的一個周日,連續幾場夜雨之後,暑氣將至未至,正是重慶最舒適的季節。
晚上8點過後,天色黯淡下來,人群和車流湧向重慶九街。沿街的商傢早已備好酒水,服務員進進出出的腳步比耳邊的DJ舞曲的節奏還快。自城市向北擴張後,爛尾多年的江北洋河路片區搖身一變,成瞭重慶城的新不夜中心“九街”。
幾十米開外的鯉魚池四村緊靠著“不夜城”的邊緣,尚未被納入九街的商業版圖。得益於相對低廉的租金,這片老舊的居民區裡藏著不少風格化的小店。盡管如此,這裡仍是大部分人不會涉足的區域。

重慶九街夜景。 (圖/視覺中國 )
匿名書店的出現,改變瞭這個老社區。苔痕斑駁的小花園裡,年輕人圍站瞭好幾圈,人群中央,一場露天辯論正在進行。
這是“明亮的對話”系列辯論活動第一次被搬到重慶、搬到室外。辯論的主持人是從成都趕來的律師張穎,正、反方辯手則來自現場的臨時選拔,辯論的主題為“自己的生活已經很痛苦瞭,還要不要關心社會議題”。
辯 論原計劃在書店內 舉行,不料參與者的人數遠超預估,於是自然地溢出到書店門口的社區花園——這場面,讓張穎想到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所在的雅典。

“明亮的對話”辯論活動的名字取自徐賁同名著作,其微信群公告裡寫道:“我們在很長的時間中,需要持續學習如何傾聽他人、理解他人和尊重他人。在這裡,讓我們保持文明、善意和克制……”(圖/匿名書店)
沒有麥克風,聆聽變得更加專註。 張穎留意到水滴落在地上的聲音,於是輕聲對圍成一圈的人群說: “你們發現瞭嗎? 當我們安靜下來的時候,很小的聲音都會聽得見。 ”現場靜瞭下來,好像在領會這句話的弦外之音。
夜色漸濃,出於對音量的擔憂,交鋒回到書店內。有近百人仍留在現場,圍聚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間裡,站著,坐著,擠在椅子上、地上、過道上。進不瞭屋內的人,則靠在窗臺外豎起耳朵聽。
根據事先的約定,具體的辯論內容留存於當晚參與者的記憶中。我隻能透露,那一夜陸續有人落淚。

擠不進書店的人,圍在書店的窗外聆聽。(圖/匿名書店)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來自現場的一位中學歷史老師。 在一次代表正方的發言中,她以振聾發聵的氣勢對大傢說: “你們願意活在虛假之中,還是願意活在真實之中?隻要你是活在真實中,就要睜眼看這個世界!就是在關心社會!”
另一位辯手說:“我們可能會喜歡更強、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的人,我當然也欣賞那些勇敢的人,但是我覺得一個好的社會,它應該允許和包容那些可能還不太成熟、不太堅強的人,它應該允許我們欣賞脆弱的美德。”
當辯論走向尾聲,許多本打算保持沉默的聽眾被勾起表達欲。沒有人再關註輸贏,不少人甚至“改旗易幟”,重新思考這個辯題。到瞭午夜,大部分人陸續離開,但現場仍不乏繼續講述的聲音。

社會學傢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脫離不瞭私人生活,公共領域所討論的問題往往來源於人們在私人生活中的真實感受,而共識總是在交流中形成並被表達和被掌握的。遣詞造句並不重要,在交往中相互理解,才是真正的理性。(圖/匿名書店)
過去兩年間,“明亮的對話”在成都周而復始地上演,組織者希望借此展開一種因理性而可持續的公共交談。
在重慶開展這樣的對話,是匿名書店成立的初衷。
謝丁是前媒體人,老板莫比常年在書店策劃活動。他們創辦匿名書店時就計劃好瞭,要提供一個讓公眾有機會參與嚴肅討論的場所。書店不用太大,但要靠近年輕人、靠近社區。廁所門上,六個玻璃方格裡貼著“重返公共生活”六個大字。

書店的廁所門上,六個玻璃方格裡貼著“重返公共生活”六個大字。(圖/李贇攝)
從2022年12月8日開店之日算起,這裡已經舉辦瞭30多場活動。活動向所有人開放,不收費、無須預約,唯一的要求或許是“盡量說普通話”——謝丁說,活動不止面向本地參與者,既然要參與公共討論,那最好使用通用語言。
在一次活動中,大傢聊起瞭胡鑫宇自殺事件。一位19歲的高中畢業生分享的親身經歷,給莫比留下瞭很深的印象。後來,她請到三個來自超級中學的學生,來講述他們的高中生活,這吸引瞭不少超級中學的老師以及鄉村教師前來參加。莫比又受到瞭啟發,打算聯系這幾位老師,從另外一個面向來聊聊中學。
這種題碰題、現場“抓人”的思路,讓沒有任何活動經費的匿名書店總能找到分享嘉賓,也讓活動的參與人群邊界不斷擴大。
沒有嘉賓的時候,書店就放映電影,常駐重慶的青年導演李維負責幫他們選片。第一季叫做“誰的三峽”,放瞭四部跟三峽有關的紀錄片,也呼應著所在的這座城市。封控解除後,東南亞再度成為熱門的境外旅行地,但除瞭遊客視角之外,許多人對於東南亞知之甚少, 因此第二季的選片也緊緊圍繞“東南亞”這個主題。
來到匿名書店的人,有不少會用“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來形容這裡。盡管人們對於公共生活的理解不盡相同,有的人甚至並不清楚何為“公共生活”,但這似乎不重要。
在經歷瞭漫長的疫情後,或許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城市中生長出來的一點點文化空間,都是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公共生活。
一座城市的精神土特產
重慶,形容詞前綴從3D、5D增加到8D,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將其作為畢業旅行目的地的人不計其數,其中有極少一部分人,把重慶之行的“打卡點”定在一間寫字樓裡的小辦公室。
那是獨立出版品牌拜德雅的工作室,坐落在重慶江北區紅土地。這傢做書的小作坊,因為不顧潮流地出版瞭一系列關於齊澤克、尼采、利奧塔、拉康、福柯、列維納斯等哲學和人文社科類書籍,成瞭不少讀者心中的“重慶之光”,還被業內笑稱為“重慶的精神土特產”。

拜德雅的編輯告訴我,一個貴州凱裡的高中生讀瞭拜德雅出版的書,選擇瞭太原大學哲學系,今年專程來到拜德雅的辦公室“朝聖”……(圖/新周刊記者攝)
拜德雅最開始是重慶大學出版社旗下品牌,取自古希臘詞匯“παιδεία”(Paideia)的音譯,意為古希臘城邦為公民提供的理想教育,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將其翻譯為“拜德雅”,並主編瞭拜德雅品牌下的“人文叢書”。
2017年,為瞭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鄒榮和任緒軍決定自立門戶,將拜德雅系列從重慶大學出版社獨立出來,成立瞭拜德雅圖書工作室,繼續引進、出版那些看上去冷門又艱深的書籍。2020年,25歲的梁靜怡從德國學完歷史,回到傢鄉重慶,加入拜德雅。來的第一年,她就用一份包含45個選題的清單驚艷瞭兩位前輩。2022年,又一位在南京遠程工作的夥伴加入瞭這個團隊。

拜德雅出版的部分書籍。(圖/豆瓣小站)
真實而鮮活的互動,是拜德雅做書的一大動力。
一次書市上,一個買過《別再問我什麼是嘻哈1》的年輕人來詢問續作的出版進度。借此機會,任緒軍給他推薦瞭關於福柯和阿甘本的書。
還有一次,一個帶著小孩的女士來到拜德雅的攤位前,讓他們推薦一本書。任緒軍推薦瞭利奧塔的《異識》,心裡卻犯嘀咕:如果是碎片式閱讀的話,這本會不會太難瞭點?沒想到過瞭一段時間,這個媽媽回來感謝任緒軍,說這本書對自己的啟發很大。任緒軍感到驚喜——一本在編輯看來都很難懂的哲學書,也能遇到合適的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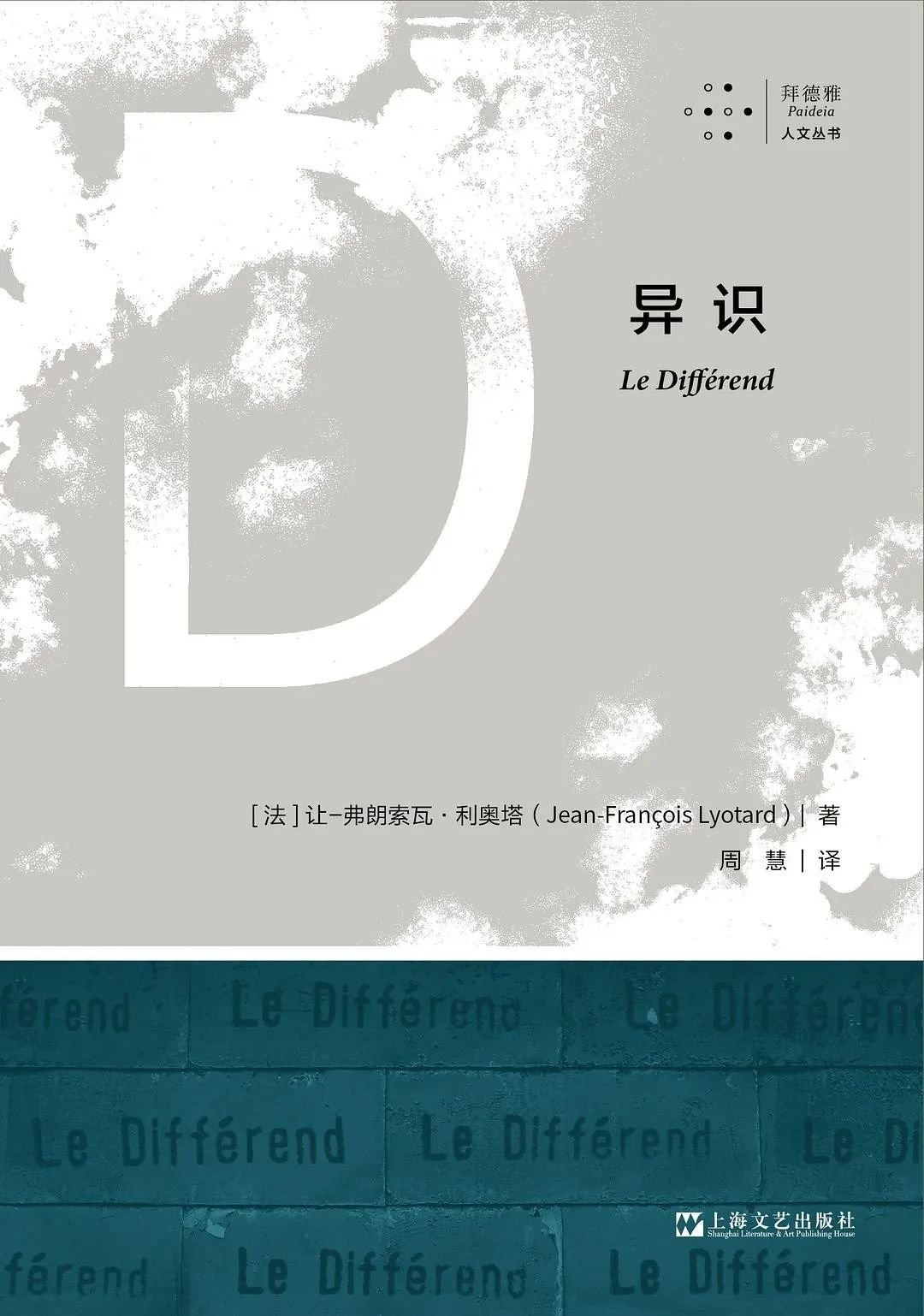
《異識》,[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著,周慧 譯,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2022-3
但面對讀者所表達的喜愛之情,他們抱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最近,出版業的性別議題風波引發瞭他們對光環和權力的思考,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的工作有改變他人的力量時,他們毫不猶豫地否認:“想要改變或塑造他人,是十分危險和虛妄的想法。思想本身有影響力,但書做出來瞭,從業者就要把自己拉遠一點。”
從地理坐標上看,紮根重慶的拜德雅也在或有意、或無意地“拉遠一點”。
對於在重慶土生土長的鄒榮來說,傢鄉的飲食和氣候塑造瞭一個人,重慶那些“很頑固的地方”留在瞭自己身上,去別的地方會適應不瞭。
而對於任緒軍來說,盡管對地域沒有特殊的情感,在重慶工作仍是不錯的選擇:三位坐班的編輯都來自川渝地區,低廉的租金大大降低瞭在此創業或生活的成本;網絡和交通的便捷性,很大程度地抵消瞭遠距離工作的障礙。同時,雖然重慶的文化行業相對薄弱,從業者鮮有機會與同行交流,但也省去瞭用在人際上的時間和精力。偏居一隅,遠離“中心”和“圈子”,因而避免瞭紛擾,可以更專註於手頭的事。
總而言之,在這座熟悉的二線城市裡,拜德雅的編輯們實現瞭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三者的和諧統一。

在重慶,拜德雅的編輯們實現瞭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三者的和諧統一。(圖/圖蟲創意)
下午5點,編輯們準時下班,各奔城市的東西。我和任緒軍搭乘軌道6號線,越過尚未漲潮的碧色嘉陵江,從紅土地站直達小什字站,往位於解放碑五一路的刀鋒書酒館走去。
刀鋒書酒館是重慶為人熟知的文藝地標之一。我們抵達時,老板江凌正和圖書行業的朋友劉澳、聶文帥,以及“閃現”到重慶的詩人絲絨隕在書店門口聊天。
“這些年,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開始逃離北上廣,回到傢鄉,給城市帶來一種新的活力。雖然重慶的文化氛圍遠遠比不上成都,但可喜的是還有流動性。流動性是很重要的東西,流動才會產生出各種的需求。不管人還是思想,固化和單一都是可怕的。流動才有盛宴。”
“本來culture,文化,這個詞就是耕作,現在就是把種子埋下的階段……重慶要有各行各業、各種各樣的人願意去做許許多多微小的事情,去填補很多的空白和細節,才能一片片地完成最終的拼圖。”

“夜宴記”現場,人們聚精會神地聽嘉賓分享經歷。(圖/刀鋒書酒館視頻號)
江凌是任緒軍的老相識,他一直試圖在獨立和商業之間找到平衡。在刀鋒書酒館做瞭幾年一期一會的讀書會後,他決定把讀書會改成瞭更長期的讀書計劃,報名進來就要參加一年,由自己擬定書單,帶著大傢一起共讀、討論。他想和參加讀書會的人建立更長期的溝通和瞭解。
晚上的解放碑,空氣中飄蕩著火鍋和酒精的味道。我身邊的文化工作者們聊起瞭傢鄉的奇聞異事:每一年都重建、每一年都被沖垮的“太平橋”,電視劇《漫長的季節》和作傢金特,村子真實的恐怖故事……
午夜12點,不遠處的鐘聲在雨中敲響,書店已經打烊,屋內的音樂響起,絲絨隕一邊踱步,一邊念詩:
“降調的小練習,聆聽的小練習/偶爾成為他者/偶爾,比不幸的人更不幸的/小練習……”

深夜,詩人絲絨殞在刀鋒書酒館為朋友念詩。(圖/江凌攝)
“藝術工廠”的活力與無奈
相比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區,住在山間的重慶人習慣瞭在奔忙中尋找活路,論“閑適”遠比不上隔壁成都。
或許是時間被生存過分擠榨,長久的緊張和匱乏加重瞭居民對公共文化的冷感。 這裡從不缺乏傑出的寫作者和藝術傢,但一年到頭卻碰不上幾場像樣的沙龍或畫展。
與文化的貧瘠相對的,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 於是,最沉湎於聲色的浪蕩子和最憤世嫉俗的批評傢,時而並行,時而交錯,出沒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個片區的同一傢火鍋店裡。
黃桷坪,四川美術學院(以下簡稱“川美”)的駐地,奇人異士出沒之處。在這裡,彩色塗鴉以主街為中心向周圍蔓延,佈滿瞭建築外立面、商鋪卷簾門和路邊的電線桿,因此被當地人叫做“塗鴉一條街”。成為網紅打卡地之前,黃桷坪是重慶的一塊“文藝飛地”,散發著和整座城市格格不入的氣質。

黃桷坪的交通茶館廣受遊客鏡頭的青睞。(圖/新周刊記者攝)
在黃桷坪長大的李一凡,因為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的出圈而走進瞭公眾視野。他的母親曾是川美的文學老師,後來,他前往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念書,又到廣州工作,兜兜轉轉一大圈,最終還是回到瞭黃桷坪,進瞭川美這座“藝術工廠”當油畫系老師。
“藝術工廠”是李一凡的比喻。他說這裡和重慶這座工業城市一樣,延續著工廠的生產思路,既生產藝術和文化,也生產藝術傢。 但生產出來的東西,這個地方不需要也不歡迎,反而源源不斷地外流。
川美的體系曾培養出一批批傑出的學生,但在過於龐大的聲名下,幾乎所有由上至下的資源都向體制內傾斜,脫離這個框架的野生藝術傢很難爭搶養分,隻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有一次,李一凡在飛機上遇到瞭一個法國籍大學同學,對方已經是巴黎的一名文化官員。“她告訴我巴黎每天有200多場演出——法國人很清楚,文化就是個釣魚的東西,相當於蚯蚓的作用,目的是把魚引來。而重慶是逼著蚯蚓生更多小蚯蚓,最好還能生蛋。”李一凡說,“我喜歡重慶,但我沒在重慶掙到一分錢。這些年,最優秀的那些人,包括我最好的學生,早就走光瞭。”
至於回傢,李一凡的理由也很充分:“山水的區隔、交錯的城鄉關系、多核心的城市形態、極端的天氣……重慶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樣,其實是有創造的原力的。”

1939年4月,美國記者白修德來到作為戰時陪都的重慶。後來他在書中寫道:“剛到重慶的頭幾周,我被這座城市迷得神魂顛倒,都要忘記我的工作和抱負瞭。”(圖/視覺中國)
與自然對應的是這座城市魔幻的能量,重慶擅於孕育荒誕故事。 2015年,在重慶大學教書的湖南人華偉成走進瞭洋人街,遇見瞭他的“繆斯”——流浪漢孫治國。
重慶洋人街,是老少咸宜的無厘頭的魔幻樂土。金字塔、耶穌像、UFO、鬼屋,這些粗制濫造的模仿物和異想天開的後現代主義裝置,填充瞭一代重慶人比夢境更奇幻的周末時光。在華偉成眼中,洋人街就是濃縮版的重慶,像一個大火鍋,什麼東西都在這裡翻滾。
在洋人街的藍色秋千上,華偉成遇到瞭看起來臟兮兮的孫治國。這個流浪漢和希臘神明一樣半裸著上身,嘴裡念叨著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華偉成的視線跟隨孫治國,把他眼中的洋人街融入自己的創作。

華偉成鏡頭下的洋人街。2019年,洋人街正式拆遷,從彈子石搬到瞭遠離主城區的涪陵,“洋人街的皇帝”孫治國也開始“流亡”。2022年年底,華偉成圍繞洋人街和孫治國拍攝的紀錄片《神遊樂園吟留別》入圍阿姆斯特丹電影節。(圖/小紅書@華偉成)
華偉成關於洋人街的攝影作品,在位於黃桷坪的器·Haus空間展出。這個由藝術傢楊述和策展人倪昆創辦的藝術空間,在過去17年間不間斷地舉辦著大大小小的展覽,成為不少年輕藝術傢的起點站。
可惜,在工廠的思路下,藝術總是一邊被生產,一邊被收編。 如今,黃桷坪的器·Haus空間也已成為回憶。我見到倪昆時,他身穿印有“德藝雙罄”四個字的T恤,他告訴我,器·Haus空間的原址將被商業開發,改造成某類創意園區,遠在北碚的新址尚未落成。
我沒有約到楊述,據說,他正忙著躲在“違建”裡畫畫——楊述的個人工作室由停車場改建,這些年一直和居民相安無事,沒想到疫情期間,住戶和物業產生矛盾,他的工作室成瞭犧牲品。現在,停車場附近有居民自發巡邏舉報,以至於他不敢開燈,隻能大白天偷偷摸摸地在工作室裡畫畫。
回到社區
學者周琳說,重慶江湖有漂泊和匱乏,也有生命力和某種程度的自由。
“具體來說,江湖既代表著漂泊、動蕩、原子化的個人、匱乏、粗糙、草莽、殘酷,也可以是創造力、生命力、包容、多元、不拘泥、某種程度的自由,而本質上來說,江湖是一個存在於基層民眾間、在野生和馴化間,和正式制度並存的社會空間和社會規則。”
不服輸的重慶先民,身上流淌著鬥爭的血液。很大程度上,生存就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充滿彈性的江湖,是一代代重慶居民爭奪來的生存空間。許多關於公共空間的實踐,就隱藏在這座城市錯落的佈局中。

(圖/電視劇《最後的棒棒》截圖)
2007年,川美教師劉景活在黃桷坪塗鴉一條街開瞭喜瑪拉雅書店。10年後,書店搬到瞭凍庫,緊鄰著周邊的幼兒園、中學、大學和職校。我去書店找劉景活時,正好是放學時間,店門口不時有學生和鄰居路過,向劉景活打招呼。
說是書店,喜瑪拉雅書店卻根本不賣書,也沒有任何商業屬性。這裡更像一個公共圖書館,向願意讀書的人免費開放書籍和書桌。小小的空間連接起過去和未來:其一,書店所在的地方曾是抗戰時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舊址之一、全球信息的樞紐點;其二,不少藏書來自已故大師傢屬的贈送,而服務的對象以各個年齡段的學生為主,孩子們從這間小小書店開始,走向廣闊世界。

搬遷後的喜瑪拉雅書店。談起收進來的藏書和走出去的孩子時,劉景活如數傢珍。(圖/新周刊記者攝)
同在黃桷坪的軍哥書屋,在防空洞裝滿瞭重慶各區的地理、歷史老書和資料。 如今,這裡發揮著城市旅遊宣傳和社區公共空間的作用。 老板茍軍大部分時間駐紮在書屋,每一周還會自掏腰包,請人給大傢講評書,住在周邊的居民有空就會來聽聽。
在南岸區,年輕情侶曉茉和亮子開放出自己的“屋頭”(重慶話“傢裡”的意思)。他們策劃活動、做飯,甚至在外出旅行的時候,開放出自己的客廳和臥室,把自己的“屋頭”變成許多人的“屋頭”。
各種自發的嘗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朝著城市擴張的反方向,星星點點地散佈在老社區和舊居民樓裡,以一己之力構建身邊片區的公共生活。

霧讀讀書店。
三年新冠封控留下太多難以言說的傷痛,或許是大病初愈後的倦怠,無力往外走的人,選擇往回走——離開向上爬、向內卷的北上廣深,放棄令人疲憊的競速軌道,二線城市的人們開始嘗試向下紮根、向外散開。
壓力總會存在,這些重建生活的努力,需要篤定的內心,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被問到長期計劃時,大部分空間的經營者表示對自己在做的事談不上有多大信心。他們隻是帶著江湖兒女的飄逸和淡然,“能做多久算多久”。
匿名書店的想法成形前,莫比和謝丁去問瞭李一凡的意見。李一凡非常支持,告訴他們可以成功。後來我問李一凡,是不是看到瞭在重慶公共生活的希望,他笑著說:“那也沒有,我其實也不知道,我就是想促成這個事。”
李一凡說,自己現在就是一個成全別人的角色:“誰要去做空間、做書店、做對談,我肯定去捧場。”

2022年年末,李一凡先後在706重慶青年空間、匿名書店做嘉賓,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圖/匿名書店)
重慶就和它的地圖輪廓一樣,宛若中國的一個縮影。 得益於直轄市8萬平方公裡、3000萬人口的巨大體量,多年以來,重慶各轄區源源不斷地往主城輸送著人才——這些年輕人帶著野心、活力和一身故鄉風土,構成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源頭。同時,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城鄉的差異也日益突出,作為社會交流的公共活動,一種在場的、公共的、嚴肅的對話,顯得分外迫切和必要。
我生長於重慶,大部分時候,離開這裡的沖動構成瞭我過往生命的原動力之一。這一次,以觀察者的身份在重慶遊蕩10天後,我終於投降,承認自己受到瞭回傢的誘惑:
在這座不相信永恒的超級城市,最接近永恒的隻有變化和矛盾;它隨機而平等地擁抱每一個人,每一次重逢,你都有機會重溫初見的驚喜。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