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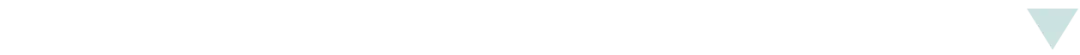
近一個月,三條“富士康”相關的消息接連引爆輿論:
一則是7月下旬,臺灣媒體中時新聞網稱,由於在印度生產線制造的蘋果手機良品率僅50%,且測出大腸桿菌超標,富士康正將部分產能重新遷回中國,全力生產iPhone 16。
與此同時,河南日報載,7月22日,富士康與河南省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在鄭州打造新事業總部大樓。河南省長王凱直言,“希望富士康堅定投資河南信心”。兩天後,富士康母公司鴻海科技集團發出公告,稱新事業總部項目一期投資達10億。
然後是8月初,內地的社交媒體上,鄭州富士康突擊“高薪招工”、“兩周進場新員工至少5萬人”的消息開始刷屏。視頻中,火紅的招聘易拉寶立在富士康廠區門口,大字寫著:“加入我們,夢想在這裡起航。”
後疫情時代,富士康曾加速將產能撤離中國,轉移至印度、東南亞等地,一度引發國人焦慮: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江湖地位,可能就此不保?
如今一連串“回暖”的信號,實在耐人尋味。網友驚嘆,“富士康太牛瞭,一下子解決5萬人就業。”觀望中的香港媒體也評論道,“富士康‘回歸’中國內地。”
所以,富士康真的回來瞭嗎?

上個月底,在已經嚴重磨損的手機屏上,許寶坤看到一條讓他振奮的招工信息:富士康把產能從印度遷回中國,正在鄭州大量招工。
他是91年生,初中學歷,老傢在河南駐馬店農村。這條招工信息無疑給賦閑一個多月的他打瞭一劑強心針,他當天就出發前往省會鄭州,打算趕緊在鄭州富士康超級工廠找點事做。
這個超級工廠位於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是富士康在鄭州三個廠區中最大的一個(以下簡稱港區富士康),也是全球最大的蘋果手機生產基地。工廠距機場僅6.3公裡,每天至少有3趟航班為它運來高端零部件,也有五六趟航班將其產品出口到全球一百多個國傢。這裡占地560萬平方米,相當於784個足球場,沿著寬闊筆直的雍州路兩側,分成從A到K的多個子廠區。

G南區旁就是港區富士康的招募中心。8月12日早晨,距8點正式開門還有十幾分鐘,等著面試的新工人已零散排出十幾米,有人拉著行李箱,也有人在馬路牙子上或蹲或坐。電子喇叭反復播報著一個男低音的防騙通知:“未穿藍色馬甲的不是工作人員,不要理會,避免被騙、丟失財物或無法入職。”
距招募中心稍遠的路邊,站著三三兩兩的小中介。一旦出現新面孔,中介們就湧過去追問“進廠嗎”,試圖努力把對方拉進自己的招工咨詢群。群裡的富士康招工廣告寫著,招工的年齡區間從18到48歲,“不查學籍,不查流水,今天返費8000,小時工26,免費被子3件套+50元車補”。
“現在每天一千多人面試肯定是有的。”一個中介向鳳凰網表示。
這個8月,富士康大門敞開,工人嘩嘩湧入——每年7-9月是這裡的招工旺季,招的主要是臨時工,又細分為小時工和派遣工。“富士康的臨時工收入比正式工高。”另一個中介表示。
其中,小時工按照工作時長計價,進廠後先和富士康正式工同工同酬,差價會在每月28日發放;派遣工也先和正式工同工同酬,但在工作一定期限,比如3個月後,可以領取一筆額外的獎金,即“返費”。

在港區富士康附近的招工中介報瞭名,經過簡單的面試、培訓,許寶坤絲滑入職港區富士康,成為一名臨時工。他被分去瞭流水線組裝iPhone 16,這是蘋果公司計劃在2024年9月10日全球發佈的新品。
緊鑼密鼓的蘋果籌備季裡,富士康成瞭一個巨大的就業蓄水池,那些顛沛流離的低學歷農民工、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大齡”的職場失意人,通通都被收留。
得知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費漲到8000元後,22歲的謝俊也從鄭州傢中來到瞭港區富士康。
他是2024應屆本科畢業生,學的是土木工程。房地產行業曾貢獻瞭中國近25%的GDP,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就業蓄水池”,但如今,在被外界調侃為“爛尾樓之都”的鄭州,謝俊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
富士康成為他短期過渡的首選。富士康的員工級別分員級和師級,他被定級員一,富士康最低的普工級別,和初中學歷的許寶坤一樣,底薪2100元。
從2024年這個季度看來,就業指標是蓬勃向上的,比如招聘人數的增加、臨時工工資的上漲、面試通過率的提高。金可誠是鄭州一傢大型人力資源公司的負責人,多年來一直為富士康招工。他表示,今年5月到8月,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費從4500元一路漲到瞭最高8000元,小時工的價格也從22元每小時漲到瞭最高26元,現在進富士康工作3個半月,可以拿到將近2萬元,“這在鄭州屬於比較高的收入”。
招工旺季的巨大漣漪,迅速擴散到瞭毗鄰港區富士康的沃金商業廣場周邊:一位60歲的電三輪司機對鳳凰網表示,以前一天拉不到100塊,現在一天能拉200多;一傢服裝店的店長也說,營業額在半個月內上漲瞭50%。
“人回來瞭,生意就回來瞭。”服裝店裡,這位40多歲的個體戶女老板揚起眉毛說。


說“回來”,是相對“離開”而言的。
前兩年,“富士康重倉越南印度”“富士康加速撤離中國大陸”的新聞傳遍瞭財經媒體——對鄭州經濟而言,這無疑是個沉重的消息,畢竟富士康在2018年曾以一己之力占去鄭州超過80%的出口額——接著,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2024年一季度,河南手機出口量斷崖式暴跌61%,導致一季度河南出口額大跌23%。
在因富士康而興的鄭州港區,人們密切關註著和中國制造相關的國際大事,哪怕一個車間工人也會在茶餘飯後不時談起“印度制造”,以及自己在某種意義上的競爭對手:印度工人。
“印度勞動力比中國更廉價。”嚴楓華是一位在鄭州富士康工作瞭12年的老員工,在她看來,富士康在人口更多、更年輕且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建廠,不啻為一個理性選擇——去年,印度超越中國,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傢。印度全社會平均年齡隻有29歲,而中國是39歲。另外,印度工人的工資不到中國工人的三分之一。

蘋果的全球戰略部署證實瞭工人們的推論。iPhone是蘋果最賺錢的產品,2023年底,印度生產的iPhone占到瞭14%,如果不出意外,幾年後這個數字會達到25%——而在2022年之前,超過96%的全球iPhone都是在中國大陸組裝的。
談及印度這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時,鄭州富士康的工人多數抱有善意的理解。“中國也曾是一個農業大國,也是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嚴楓華說。“東南亞要發展,印度也要發展,就像中國改革開放時吸引外資一樣,你不可能阻止人傢。”在富士康工作瞭14年的李林說。
但意外終究發生瞭:在素有“外資墳場”之稱的印度,富士康的發展一路坎坷。2024年7月23,一則來自臺灣中時新聞網的消息稱,“印度廠iPhone代工的良率(僅5成左右)”且“衛生管理(大腸桿菌超標)仍存在問題”。盡管這則消息並無確證,另一些現實卻確鑿無疑:
2023年7月,富士康母公司鴻海對外宣佈,退出與印度金屬石油集團韋丹塔合作的195億美元芯片制造計劃。當時路透社、彭博社等報道,原因與該工廠建設緩慢、補貼遲遲不發放等有關。在2024年的夏季高溫中,富士康的印度工廠還被政府要求減少30%的用電量,斷電成瞭傢常便飯。諸多“不測”,讓印度富士康的產能遠不抵預期。

富士康在印度建廠後,嚴楓華的一些同事曾被派去支援。回到中國後,他們的感慨之一是,用同樣的機器,在中國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印度生產不出來,“我們對品質的管控標準,他們理解不瞭”。感慨之二是,在印度,富士康的政策很難執行下去,哪怕這些政策合法——一度,印度卡納塔克邦為瞭配合富士康的生產,將政策改為允許12小時倒班、女性上夜班,但憤怒的工人們燒毀瞭法案副本,當地裝配線工人帕德米尼告訴媒體他無法容忍高強度的生產線:“我必須活著才能工作。”
比起印度,中國富士康堪稱效率的王者。嚴楓華記得,一次,鄭州富士康要向員工宣導品質政策,決定大約在當晚8點出臺,到第二天,這項品質新政的打印版本已經貼滿瞭車間,並在每個廠房門口的電視屏和LED屏上滾動播放,早晨8點開會前,員工們每人都領到瞭一張,由廠長帶領大傢現場背誦:
“全面品管,貫徹制度,以提供客戶需求的品質。全員參與,及時處理,以達成零缺點的目標。不接收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時至今日,這段“箴言”仍不時浮現在嚴楓華腦海裡。
但對富士康來說,將低端產能向印度等地轉移,或許已是長期趨勢。近日,財富中文網分析指出,此次富士康產能回遷是為瞭保障iPhone 16系列的平穩出貨,這充分肯定瞭中國代工廠的能力和價值,另一方面,這也是給印度方面更多的時間做準備,以便在將來承接更多的產能。
8月17日,富士康董事長劉揚偉宣佈,2025年將加大對印度的投資。
許寶坤沒有關註這些經濟新聞,他更關註的是印度的國民性。通過那臺799塊買來的小米手機,他刷到過包括種姓制度在內的科普知識,他得出結論:“印度人比較慵懶,會享受,不會為瞭錢太拼命,不太好管理。”
“中國人對名利看得更重,用這個就可以管理好。”他做瞭一個數錢的動作。

掙錢一直是許寶坤生活重大的母題。18歲那年,他離開駐馬店老傢去北漂謀生,因為他被《士兵突擊》中的許三多打動,想成為下一個王寶強,“他長相也普通,傢境和我一樣,對不?”
在後奧運時代蒸蒸日上的北京,許寶坤努力掙錢:他在八一影視基地做過群演,演一個國民黨反派,日薪90元;他去工地打過雜,也通宵裝卸過快遞;打過最久的一份工是當小區保安,月薪4000元,不累,但那份工作時常讓他自卑——開好車的業主有時會兇他,“他們看不起我們,脾氣很大”。
而在富士康,按照招工時25元一小時的承諾,即便不加班,每天隻工作8小時,許寶坤也能拿到200元的日薪。一進廠,他的工牌裡就被充上瞭400元飯費,這是富士康提前預支給工人的,發工資時再扣,“對沒錢的人很方便”。宿舍是6人間,150元一個月,水電免費,“很幹凈”,還有兩個廁所,遠勝日結房和橋洞。如果表現良好,他還有機會轉成正式工,領到五險一金——他以前的工作從未有過五險一金。
許寶坤感到自己被賦予瞭尊嚴。“你感覺自己就是個正常的工人,沒有那種痛苦、自卑的感覺。你是來掙錢的,我也是來掙錢的,大傢都是平等的。”

當被問及富士康最好的地方,幾乎所有工人第一時間都下意識脫口而出——“富士康從不拖欠工資。”每個月的7號,富士康一定會準時發工資。“不管行情好不好,富士康不拖欠,不克扣。哪怕你隻上一天班,也能拿到這一天的錢。”嚴楓華說。
在這裡,如果正式工被裁員,會有N+1賠償——這在勞工階層並不多見,前富士康員工王雄飛的兩個朋友最近被一傢私人門窗廠開除,沒有領到一分錢賠償。進廠初期,他經歷過一次2小時的停電。那2小時,富士康也算進瞭工作時間。
況且,對都是河南人的他們來說,這還是一份在傢門口的工作,再不用背井離鄉北上南下打工瞭。
盡管2010年從深圳內遷到鄭州、成都等地主要是出於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但無意之間,富士康引領瞭中國制造業的一大風潮:離土不離鄉。
“在傢門口就能得到和走出去一樣的工作——待遇一樣,環境一樣——這點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對有孩子的人。”一直參與富士康招工的金可誠說。
當時鄭州富士康已經能輻射到開封、許昌、焦作、新鄉、洛陽等地,吸引全河南的勞動力。河南的一些縣甚至開通瞭定制車,從縣城直接開到港區富士康,天天發車。根據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數據,2011年,河南省內務工人數首次超過瞭省外。
散落在全國各地的不少河南打工人因此返鄉,進入富士康。他們往往來自農村,傢境不佳,學歷不高,“一般就是初高中”。
李林在2010年加入鄭州富士康,並被送到深圳富士康短暫培訓。那一年,深圳富士康以“十幾連跳”揚名世界,還因此背上“血汗工廠”之名,但對瞭解過煤礦工作的李林而言,這已經是自己當時最好的選擇,“富士康的收入比不上煤礦,但沒那麼辛苦和危險,工作環境也更好”。
“富士康是很好的廠,就算跑到廣東、江蘇,這樣的廠也是數一數二的。”許寶坤感慨。
十年間,在港區富士康周邊,一個龐大的“富士康城”逐漸成型。村民在拆遷後搬進瞭高層安置房,酒店、酒吧一條街、大型超市、KTV和服裝、餐飲店逐一出現。

金可誠表示,制造業用工人數和周邊服務業人數比一般是1:1.2。也就是說,1個富士康的工人,會吸引來1.2個人為他提供衣食住行服務。這相當於最高峰時,鄭州富士康養活瞭70多萬人。
對河南人來說,這是托底的安全網、最起碼的念想——再不濟,還可以去富士康。

作為鄭州富士康的第一批員工,王雄飛和李林一路見證瞭公司這些年的起落興衰。
“河南是人口大省,當時制造業不發達,就業條件很差。”他們記得,2011年3月港區富士康正式投產時,周邊很荒涼,廠房周圍的田野裡後來還在種玉米、小麥和花生。這裡位於鄭州市所轄中牟縣,土質是沙土地,風一刮,身上都是土。當時一些廠區還沒有食堂,周邊攤販甚至可以進去賣小吃。
也是在2011年,他們開始生產蘋果的iPhone 4S,做的是焊接工作。iPhone 4S很快成為蘋果的經典和爆款機型之一。到2014年左右,港區富士康的員工數達到瞭30多萬。進富士康前,王雄飛在鄭州的一個食品廠短暫待過,一天工作12個小時,到手1000元左右,但富士康讓他的工資瞬間漲到3000多元。“富士康來瞭,周圍的工廠工資都漲瞭。”他說。

但這幾年,老員工李林發現自己的收入並沒有隨著GDP和物價同步上漲。2017年,他的底薪是2100元。2024年,他底薪是2400元。他給鳳凰網展示自己手機上的納稅記錄。作為一個鄭州富士康14年的正式工,今年上半年,他的月平均工資為4500多元。
最高的一個月是3月,近7000元,其中包括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年終獎。最低的一個月是2月,因為無班可加,隻拿到2400元底薪。
2023年也是如此。這年春節後直到5月,鄭州富士康的業務慘淡,員工想加班幾乎都沒有機會,很多正式工每月隻能拿2000多元的底薪。盡管每天圍著iPhone系列轉,直到現在,李林還沒有用過一部蘋果手機。
“今年不比去年強多少。”他表示,5月前,自己單月加班時長隻有3-4個小時,到瞭臨近旺季的6月,加班才多瞭一些。
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李林發現,富士康的工人越來越少瞭。iPhone的尺寸、色差監測和螺絲裝拆等工序,以前靠人工,現在靠機器。“前端隻需要幾個人放物料,傳動帶把它們送到機臺,機械臂抓取後自動加工。”
“這幾年機器多瞭,人少瞭。”嚴楓華也說。
疫情,是鄭州富士康的一個轉折點。盡管此前蘋果已經在將生產線轉往印度、越南等地,但疫情之後,因為地緣政治壓力、爭奪新興市場等因素,蘋果加速瞭產業鏈的轉移。很多富士康的工人就此離開。他們去往附近的其他電子廠,去送外賣,做裝修,或者再次去往南方打工。
當富士康隨蘋果加大在印度和東南亞的佈局後,國內網上出現瞭各種極端論調:“河南不缺一個富士康”“富士康走瞭就走瞭”“富士康滾出中國”……
每次看到這樣的言論,王雄飛都很氣憤——“他們不知道富士康給河南帶來瞭多少東西。”
如今,港區富士康的工人已經從30多萬降到瞭10來萬。盡管2024年8月難得迎來瞭一個用工高潮,但金可誠知道,這樣的盛況隻會持續3個月,僅如曇花一現。過去那種招工忙到晚上12點、人們為瞭進富士康當工人給中介塞錢的日子,一去不返瞭。

對於此前富士康“兩周進瞭至少5萬人”的報道,金可誠表示,“是計劃招5萬人,但目前還沒招滿”。他的觀察是,和前兩年相比,富士康今年的招人指標在下降,他的公司“利潤比前幾年還少”。
即使目前富士康大門敞開,招的也大都是臨時工。他們與人力資源管理公司簽署合同,屬於第三方派遣,幹完旺季就走。這有利於富士康在短時間內(尤其是突擊iPhone新品發佈的時刻)迅速擴張產能。但生產旺季一過,臨時工們就會像候鳥一樣離開。

2012年蘋果還一騎絕塵時,中國青年報指出,如果要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在整個世界產業鏈中,蘋果是美國的代表,富士康就是中國的代表。
作為勞動力密集、利潤微薄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的危機其實早已浮現。
毛利潤率整體在降。根據鴻海8月14日公佈的2024第二季度財報,其毛利率為6.42%。而在15年前,其季度毛利率最高曾超過10%。
在中國市場,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戶蘋果也大不如前。2024年第一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機銷量榜上,三星排第一,蘋果排第二,排名對換。彭博社引述一位專業人士分析稱,排名變化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市場競爭加劇”。
第一次看到iPhone 4S時,王雄飛曾倍感驚艷。那時他用的是一部1000多元的國產安卓手機,反應遲鈍,時常卡頓。而iPhone 4S的屏幕非常靈敏,“點哪個就是哪個”,一點不卡頓。

但現在,國產手機的性能已經跟上來瞭。2024年第二季度,蘋果手機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掉到瞭第六,排在vivo、OPPO、榮耀、華為和小米之後,四年來第一次跌出前五。
富士康也有瞭新的代工競爭者,比如比亞迪和立訊精密。如今,它們都加入瞭iPhone 16供應鏈。
長期以來,大幅減員增效、臨時工取代正式工、無人化,都成為富士康控制成本的發力方向,勢不可擋。
這引來瞭人們的憂心忡忡。“河南有9000多萬人口,無人化以後,這些人怎麼找工作,特別是學歷不高的?”王雄飛問。
如今,“富士康城”也盛況不復瞭。正值招工旺季,多傢店鋪卻已歇業,門口貼著“旺鋪轉讓”,剩下的店鋪也在下調租金。一傢女裝店負責人向鳳凰網表示,這裡曾經請瞭七八個員工,現在隻請瞭一個。另一傢女裝店最貴的商品從139元降到瞭69元,店員稱,“臨時工幹幾個月就走,不舍得消費”。2016年iPhone 7 Plus剛上市時,一個生意興隆的服裝店老板花6000多元買過一部,現在生意不好做,她用的是一部2000元的vivo。

張莊距港區富士康5公裡,是附近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很多富士康工人的廉價租房寶地。如今這裡正在拆遷,一位有100多套房的村民和政府沒談攏。進村的路因拆遷被挖得亂七八糟,加上工人銳減,他的房間出租率從當年的100%降到如今的不到30%。
他發現,張莊開始拆遷後,一些富士康的工人就離職瞭——沒瞭城中村,他們的生活成本直線上漲。
這位村民說,張莊辦事處之前組織他們開拆遷動員會,提到“你們房租也收夠瞭”。
他心想:“那是時代給我們的紅利。”

對剛進港區富士康三天的打工人許寶坤來說,公司的戰略轉型還過於遙遠。眼下,他感覺自己已經被機器人打敗瞭。
他說自己記性不好,做iPhone 16模具整合的流程,怎麼也學不會。他又被安排去撿機器人焊接後的手機,因為手速不夠快,一直堆積。身邊的同事不停幫忙,這讓他心理壓力巨大,權衡再三,他選擇瞭主動離職。
在“富士康城”一個商場的長凳上睡瞭幾晚,他還是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剛從駐馬店老傢來鄭州的他,現在又得回老傢瞭。但傢裡的地早就包給瞭別人,他回去也無地可種。

帶著全新的被褥臉盆,坐在“富士康城”最繁華的十字路口一角臺階,他幾次打開一盒已拆封的紅旗渠香煙,卻始終沒有點燃一根。33歲,初中學歷,身無長技,他不知道應該去往何方。
感覺到危機的富士康,也正在努力尋找新方向。2023年,富士康新事業總部在鄭州揭牌。當時富士康董事長劉揚偉表示,要在河南省再造一個“新的富士康”,專註於加速電動車整車、儲能電池、數字健康和機器人產業落地。
2024年8月中旬,鳳凰網實地探訪瞭未來的富士康新事業總部所在地。這裡距港區富士康42公裡,和鄭州市鄭東新區中原科技城創新孵化基地大樓僅一條馬路之隔,目前還是被圍擋攔起來的一片空地,上面覆蓋著綠色防護網,停著一臺挖掘機、一臺推土機。
旁邊一個小賣部的老板表示,富士康和河南省政府的戰略合作簽約儀式是在7月22日簽署,四天後,這片土地開始平整,“沒幾天就平好瞭”。

在旁邊的中原科技城創新孵化基地,一棟大樓上寫有“富士康新事業總部”字樣。大樓的其中兩層,就是富士康新事業總部的臨時辦公地。其中一層正對門的辦公室門口寫著“EV(電動車)制造發展中心”。
李林說,富士康一直想造新能源車,過去也有一些動作,但這次,“看來是動真格的瞭”。也有同事犯嘀咕:這個領域已經是一片紅海,現在入局會不會太遲?有人聽說比亞迪也在招工,而且工資更高,開始四處打探機會——他們想去更能掙錢的地方。
無論如何,李林選擇在富士康留下來。
十多年裡,iPhone從4出到瞭16,李林感覺自己的生活毫無變化。到點上班,到點下班,缺乏社交,人變得麻木。他已經習慣瞭鐘擺一般的生活,離不開瞭。
而有些時刻,王雄飛也在想象“回歸”富士康。在富士康工作四年多後,他選擇瞭離開,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後來他做過很多工作,比如手機分期、遊戲搬磚,還有一次,他失業瞭好幾個月,直到在鄭州開起瞭網約車——探索世界的結果是,他慢慢意識到,很多工作“比在富士康上班還累”。
“我想進富士康。”王雄飛的另一位網約車同行也這樣告訴鳳凰網。這位司機曾任職於一傢知名電商零售企業的物流部門,2022年,35歲的他在被裁和轉崗中選擇瞭被裁。他想進幾傢有物流業務的互聯網大廠,但HR的回復如出一轍:“超過35歲不要。”
當上網約車司機後,他每天早晨6點半出車,工作超過12小時,自己交社保,不安全感時刻縈繞。他也發現,這份工作並不自由——“幾點出車,幾點收車,賺多少錢,都被平臺的大數據控制得很死,每天基本不會有浮動。”
於是,曾被詬病“沉悶”“不自由”的富士康有瞭某種強烈的吸引力:它穩定,招工年齡上限寬容到瞭48歲,正式工有五險一金,離職還能拿N+1。
他們開始惦念和向往富士康,仿佛那在機器運作聲中高速運轉的流水線,奏出瞭打工史上一曲美妙的樂章。
應受訪者要求,許寶坤、謝俊、嚴楓華
王雄飛、李林、金可誠為化名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