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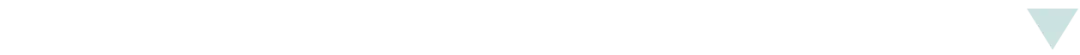
再一次,我們很可能在經歷氣候史上“最”離譜的一個夏天:
也許你清晨從貴州鎮遠的民宿標間裡醒來,發現窗外河水已經漫到三樓,連沙發也漂浮起來;也許在你山東東明6樓的傢中,忽然天色驟暗來瞭一陣龍卷風,把廚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許你去瞭川西跟團遊,結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體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變成極限逃生……
官方一場接一場的新聞發佈會勾勒著災難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來,國傢多次向災區預撥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並調動折疊床、夏涼被、傢庭應急包等中央救災物資支援前線。7月4日,中國氣象局在答記者問時表示,由於全球持續變暖加劇瞭氣候系統的不確定性,中國的極端高溫和極端強降水事件正在趨多趨強。7月14日,水利部召開新聞通氣會:今年入汛以來,全國多流域連續發生20次編號洪水;預計“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間,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發生洪水。
“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大傢開始感到無力和疲憊,這會讓人們把頭轉向一邊。”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周楚涵說。
“今年上半年確實重瞭一些,是我們做氣象災害這十年裡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負責人郝南說。
“今年整個基金會的募款項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瞭,(隻有)三位數。”全國曙光救援同盟指揮長王剛說。
在這個大江大河洪水並發、超警以上洪水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鳳凰網與6位來自民間救援隊、基金會和環保NGO的人士對話,試圖探索極端天氣導致災難頻發的時刻,面對救援人手、物資、公眾註意力等諸多缺口,我們的社會應急救援還能做些什麼?

一向快人快語的王剛,此刻就像“像素遊戲”裡的小人回到現實世界,吐詞磕磕絆絆,語速極慢。
王剛是全國曙光救援同盟指揮長、廈門市曙光救援隊隊長。接通鳳凰網電話時,他剛結束在湖南華容洞庭湖決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線連軸轉瞭二十多天後,王剛已經頭腦發昏,記不清行動路線。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時間和地點。對講機中隊友同樣渾濁的聲音,不時打斷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濫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經一直處在高度緊繃狀態。6月17日起,救援隊一連參與瞭7場水災救援:福建龍巖,廣東梅州,江西景德鎮、樂平、永修,湖南平江、華容。最多時有113名曙光隊員頂在前線。

◎ 2024年6月26日,曙光救援在江西浯口鎮救災
最難的一天是7月2號,王剛用“全線告急”這樣的詞語形容彼時——江西九江因“防汛人手嚴重短缺”,不得不發出“傢書”,號召當地人回鄉抗洪;洪水倒灌進入湖南平江,淹沒瞭近一半縣城;湖南汨羅更是出現瞭約30米的潰堤(那時距洞庭湖潰堤還有3天),當地人不得已將裝滿石頭的卡車駛入河中阻流……
那天凌晨2點50分,正在高速公路廬山服務區休息的隊伍收到求援消息,緊急會議後,他們決定兵分兩路:2車4艇繼續前往江西永修縣;主力團隊30人10車12艇攜帶水陸兩棲車連夜趕往湖南平江和汨羅地區;此外還調動瞭山東的志願者。
如果熟悉好萊塢的災難電影,你會知道難題總是接踵而至。現實也是如此。對於王剛來說,更麻煩的是“七下八上”防汛關鍵期和臺風季還沒到來,錢卻快花完瞭——截至7月17日,曙光救援的行動資金支出超過40萬,而這個民間救援團體全年的備災資金也就50萬。
到處都是錢窟窿——補充救援裝備,隊員訓練經費,日常開支,救災行動。為瞭省錢,一個月前,隊伍從廈門出發時自備瞭50箱面包、21箱自熱米飯和50張行軍床;每抵達一個地方,他們隻開三四間酒店房間供四五十名隊員輪流洗澡;休息時,女隊員住酒店,男隊員搭帳篷住行軍床。去年一年,廈門曙光積攢的礦泉水瓶和紙箱賣瞭3321塊錢。

◎ 救援人員在湖南華容縣洞庭湖決堤救災現場
7月13號零點18分,王剛和隊友終於回到廈門。與此同時,重慶暴雨引發的洪澇災害已致6人死亡。四川中北部也發出“特大暴雨”預警,部分區縣救災指揮部開始引導居民轉移避險。一天後,河南省南陽社旗縣出現瞭“超級暴雨”,三天降下瞭當地一年的平均降水量——上個月這裡還處於極度幹旱中——重旱瞬間急轉成瞭重澇,一夜之間,當地人努力澆瞭三輪水才搶救過來的玉米苗,被徹底淹死瞭。
16日,王剛一邊休整,一邊在朋友圈開始接力河南暴雨洪災的求助登記表。

“今年的氣象災害比較頻繁,發生時間也比較早,已經有好幾個國傢三級和四級救災應急響應瞭。”愛德基金會社區發展與災害管理團隊主任譚花說。
在她的觀察裡,極端天氣已經不再是國際舞臺上的倡導或者媒體傳播上的文字——他們去鄉村做項目,聽到農民講耕種習慣的改變:過去割完玉米後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時候雨就下起來瞭;以前果樹種在山腳下,現在要種到山上去,底下太熱瞭。
在救援和公益圈裡,人們還感到另一種變化也在悄然發生——持續甚至不斷加碼的災害之下,人和人之間的連接正變得疲憊而松散。更確切地說,災情獲得的關註、人力和資金支持,越來越不夠瞭。

◎ 2024年7月2日,江西永修縣,車主在拋錨的汽車中求助
可每當談起這個話題,對話氛圍立刻變得謹慎。
一則被小心翼翼提起的輿論事件是,7月5日,企業霸王茶姬向湖南華容縣捐贈500萬元,卻引來反對質疑聲。有人問,這些善款真的能幫到災民嗎?還有網友評論,災難頻發後,人們對苦難麻木瞭,“現在社會缺少聯結感及共通感,大傢都處於一種原子化狀態之下……對遙遠的他人有著很深的隔膜”。
“2021年河南水災時,老百姓對救援隊伍很尊敬,是吧?”青島紅十字同塵救援中心的負責人李延照說,他是國內最早做急流、舟艇、繩索、冰面等綜合救援技術培訓的人士之一,“以前我們說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好,(如今的氛圍是)這又不關我事,我憑什麼支援?”
2018年壽光水災時,800*800平米的倉庫幾乎裝滿瞭各地馳援的物資。而今年,據卓明信援負責人郝南觀察,“各個基金會的捐贈都挺慘淡的”(譚花形容,是“斷崖式的下降”)。不僅如此,“一些社會關註度高的災害事件,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帶來大量的捐贈”。
北京緣夢公益基金會應急救援項目部負責人王涵介紹,今年基金會收到的公眾捐款占比80%-90%,其餘是企業捐款——稱得上“寥寥無幾”,而在過去兩年,企業捐款平均占比總籌集善款的20%左右。“我們往年合作的一些企業今年甚至都婉拒瞭。”截至7月15日,北京緣夢公益基金會的南方水災項目籌款45萬,而去年京津冀水災項目時,它籌得瞭700多萬。
譚花也表示,河南“7·20”水災和京津冀水災的募集款項達到“幾千萬”,今年的南方水災目前隻募到“幾百萬”。
往年,礦泉水和方便面是不緊缺物資——災害發生一兩天後,應急方便食物的需求就下降瞭,基金會采購時務必謹慎,不然就會過剩。今年卻有不同:“好幾個地方提出來的需求是應急方便食品,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方便面。”譚花在愛德基金會工作瞭20年,這讓她感到意外。

◎ 方便面是救災時重要的應急戰略物資
應急方便食品如此,更不用提災後所需的水槍(用於沖掃淤泥)、發電機、雨鞋、鐵鍬、手推車、電動三輪車、消毒藥具、水泥等等瞭——即便是社會援助充分的年份,這些災區百姓真正所需的物品也很少被外界關註到。
變化勢必影響救災救援工作。北京緣夢公益基金會在全國共支持100多支民間救援隊,並和30多傢社會組織長期合作。“如果沒有資金,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參與很多救援行動,大規模災害的救災有運營成本。如果沒有快速的籌款能力,資金怎麼能到一線也是一個問題。”王涵說,他剛從湖南救災前線回到北京。他們今年響應瞭廣東韶關和梅州、廣西桂林、湖南華容和汨羅、河南南陽、重慶的救災與救援。
譚花所在的愛德基金會的情況是,“哪裡發生災害還是會響應,但是響應規模明顯比較小。用有限的資源,能做多少是多少”。

據郝南觀察統計,近幾年達到需要公眾募捐程度的水災大約是每年20次,而真正引起全國范圍內踴躍援助的水災隻有2021年“7·20”河南暴雨和去年的京津冀水災。甚至,有的災情信息都沒能走出當地——今年6月,黑龍江倭肯河、廣西崇左和百色都發生瞭嚴重水災,都沒能在輿論場留下什麼痕跡。
現實之一是,公眾關註度和災情嚴重性並不總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災中,華容縣因為洞庭湖決堤多次登上熱搜,得到瞭更多的關註。然而,實際上平江縣的災情遠超華容縣——郝南估算,平江、汨羅救災需求折算成貨幣價值的話,大概是華容的十幾倍。

◎ 2024年7月2日,湖南平江縣,救援隊運送被困民眾
目前國內缺少對水災嚴重情況的定級,類似地震震級——“這能讓公眾更容易理解災情到底有多嚴重。”郝南說。
現實之二是,社會捐助卻和公眾關註度成正比。這意味著,災情嚴重的地方,可能因為沒有被“看見”,從而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今年6月中旬,廣東梅州和福建龍巖水災時,當地通訊中斷,消息傳不出來,“一開始沒有受到特別多的關註”。“過瞭大約兩天,我們才發現還有很多村莊在失聯中。”譚花說。郝南提到,廣東梅州、福建龍巖受災之深之廣,其所需的救災賑濟資源是平江的好多倍——平遠、蕉嶺、武平、上杭,這四個重災縣的受災程度都比平江要嚴重。
災情聚焦,這看起來是一個大眾傳播的話題——比起事後才能被量化的災害,它更取決於在受災第一現場,是否有可以幾何倍擴散的新聞點出現。“鄭州地鐵的情況出來之後,牽動瞭很多人的心。當時還有一個在線求助文檔,每個求助信息都很緊急,大傢就意識到原來水災特別嚴重。”譚花說。

◎ 2021年7月27日,鄭州沙口路地鐵口紀念遇難者的鮮花
但這遠不止一個傳播問題。受訪者們試圖梳理“災情失焦”背後的原因:經濟環境、企業效益、災害麻木、信任危機……又都默契地點到為止。
郝南強調道,捐贈遇冷不是今年的偶發現象——2015、16年之後,公眾對災害捐贈的意願就下降瞭。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成為一名志願者,後來辭去牙醫工作,全身心投入在人道主義援助中。
郝南的語速不快,善於掌握談話的主導權。在這個極端災害日漸頻發、而大眾捐助愈加疲軟的夏天,他以不由分說的氣勢反問道:“公益組織要先做到,有沒有說清楚捐贈的必要性?公眾有那麼多的質疑,有沒有人回應、解釋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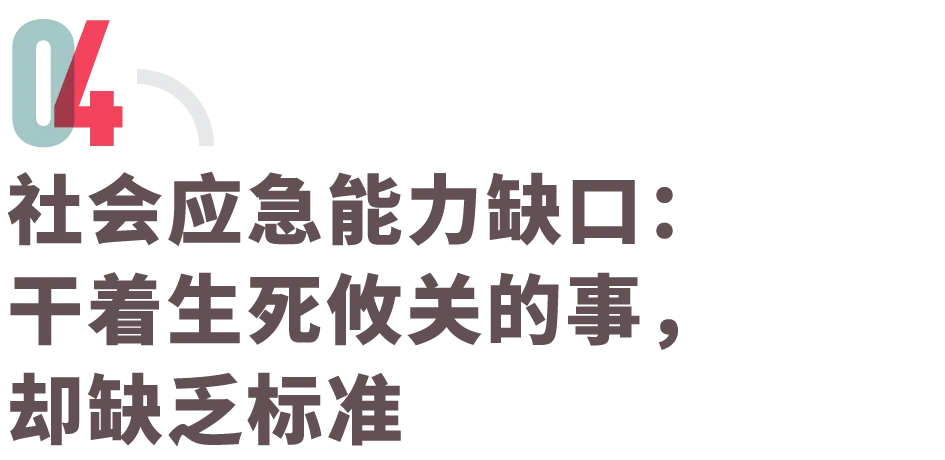
早年間,譚花和同事向企業、資助人尋求資金支持民間救援隊,總是吃到閉門羹——人們更希望善款直接用在災區百姓的身上。當時地方政府的救災能力不斷提升,也更傾向於獨立完成救援工作。
直到2021年河南暴雨,由於地區缺乏應急響應機制,有的地方甚至連備災的救援艇都不夠用。譚花說,民間救援隊在當時發揮瞭積極作用,也讓社會對它們的關註和態度發生瞭轉變。
今年的情況更不一樣瞭。“災害發生那麼多,大傢都有點顧不過來瞭,希望能夠有社會力量幫助他們。”譚花說。7月2日,江西九江江州鎮人民政府在官微上號召“全鎮父老鄉親和在外奮鬥的鄉親們”,“立即集結、迅速行動”,投入抗洪搶險中。
某種意義上,極端天氣的高發,推動瞭民間救援的發展。“(民間)水域救援是從2016、17年開始蓬勃發展的,原因是水災越來越多。”郝南說,河南水災後,民間救援隊的數量翻番,從2000支到如今的4000多支;近五年新成立的隊伍幾乎清一色是水域救援,鮮有地震、山地領域的隊伍。
“民間救援隊的優勢是靈活機動,信息來源也更迅速。”青島紅十字同塵救援中心的負責人李延照說。河南水災時,他的隊伍到瞭新鄉牧野區寺莊頂村附近,遇到一位老人從一間廠房裡遊出來。一番詢問,才得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距離此地三公裡外的村子已經被洪水圍困瞭好幾天,信號中斷,外部無人知曉。救援隊趕到後,看到房頂上站滿瞭村民,他們拿棍子敲擊鋁盆,喊著救人。隊員們花瞭兩天時間才將村裡數千人順利轉移。

◎ 2021年7月24日,河南新鄉牧野區,被淹沒的房屋
但是,極端天氣帶來更加頻發的多種災難,我們成長中的民間救援隊真的足以應對嗎?
郝南對此有很多思考:
在他看來,培養一個專業合格的救援人員需要3-5年。“我估計現在幹救援的大多數人都不具備做救援的基本素質,”他毫不含蓄地說,“我們在現場看到不少隊伍和個人確實很積極,但是他完全不具備救援的能力,他就不應該出現在現場。”
“這麼多隊伍幹著生死攸關的事情,卻沒有操作的標準,沒有技能的標準,也沒有現場指揮協調的標準。”他繼續說,這會危及救援人員和被救人員的生命安全。
一些隊伍練瞭很久的技能,但並不知道這些技能在災害現場什麼時候能用得上。“大傢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幹活。”郝南說。氣象災害救援的時機非常重要,“怎麼在水漲之前趕到現場”——“你不能等到水退瞭才去救人,這不成作秀瞭嗎?”
圈子裡還存在著另一種冒進的英雄主義。“不管能力有多大,行不行,他想去一線就會去,這叫有組織無紀律,那不就亂成一片瞭嗎?”李延照說。近些年,無論是訓練還是救援現場,都發生過民間救援隊員遇難事故。
與鳳凰網通話那天,山東東明出現瞭強對流龍卷風,風力掀翻瞭板房的房頂,造成5死83傷。如果是十年前,李延照聽說有險情,一定立刻帶隊出發。如今的他知道,等他做好準備帶隊從青島奔赴500公裡抵達東明,已經錯過瞭最佳救援時間。
“誰距離近誰優先,誰能力大誰優先。”李延照說,如果沒有相應能力,就要給專業的救援隊讓路,“不然社會應急力量會被詬病”。
這不完全是技術和態度問題,也跟資金有關。“兜裡沒錢,他怎麼提升裝備能力和救援能力?越沒錢,越想幹點活引起別人的註意。幹活越多,危險越多,傷亡越大。”李延照總結。
民間救援隊的資金主要來自於政府、基金會、企業和公眾,不同隊伍的情況大有不同。李延照隊伍的資金來源包括10%的政府支持、3-5%的社會捐贈,剩下的缺口靠他每年在全國做六七百場救援培訓等補齊。一年幾百場培訓做下來大概有200來萬。

◎ 李延照在救援培訓中
此外,政府也會購買社會應急力量的服務。服務期通常為一年,民間救援隊負責相應區域的安全隱患排查、處置突發事件、普及防災減災知識等任務。盡管國務院在2013年發佈過《關於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但政策落地情況地域差異。李延照觀察,北京、深圳的政策落地最好,“有的地方是抵觸的”。
在任何領域,如果沒有有效的機制做保障,資源註定會分配不均。就像救災時,越靠近路邊的災民得到的物資越多,越是被困的“孤島”越得不到幫助——民間救援隊同樣旱澇不均。“沒資源的,仰著腦袋隻能看天。”
盡管問題重重、困難重重,李延照還是由衷佩服做救援的兄弟姐妹——“他們從事這個事的時候,你別看他累成什麼樣,但他是享受的。”

過去幾年裡,周楚涵所在的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一直努力讓公眾理解,極端天氣出現的背後,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氣候變化。
“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包括高溫和強降水。”周楚涵說,這意味著過去沒有處理過極端天氣事件的地區和人群需要應對災害;即便有過應災經驗,很可能應付不瞭新的災害強度瞭。
現實卻是,大多數民眾,就連一些救援人員也不清楚他們的工作和氣候危機之間有什麼關系。“我當時覺得吃驚,”周楚涵說,“又可以理解,他們覺得救援是一項技能,背後的根本原因對他們來說不那麼重要。但是當你對(氣候變化)趨勢有所瞭解,會做出預判指導救援工作。”
綠色和平也在努力倡導預防災害的重要性。“把資金投入到(災害)事件發生之前,投入到在對氣候變化的適應上,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響應能力的培養。而不是事後再去救濟、修復,卷入到惡性的循環中,那會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周楚涵說。
這在業內已是共識。湖南洞庭湖救援搶險時,郝南在線上跟瞭全程。他認為當地的應急工作做得非常及時,政府安排的大巴車在傍晚6點30就開到即將發生潰壩的村子,村民也有應災經驗,配合有序。準備到位的快速反應,“減少瞭救援的工作量,也減少瞭人員傷亡”。

◎ 2024年7月7日,湖南嶽陽,卡車正排隊堵住決口
“預防(災害)具體要做什麼?是要真正的減少傷亡,”郝南說,“這不是靠救援隊,是靠一整套預警監測逃生演練體系。”
然而,基金會籌到的用於防災的資金更是少之又少——人們更願意將善款實實在在地送到災民手裡。
“我們都知道防災、減災比單純救災更重要,但是基本上沒有太多錢能用到這上面,”譚花說,“大傢更關心救災工作有沒有做到位,東西有沒有發到老百姓的手上。”
災害總是和無情、肆虐相關,但救援現場最不缺的是人們的互相守望。梅州龍巖水災時,政府部門投入幾架直升機運輸物資、轉運人員,可一些“孤島”村落並不具備起降條件。一開始,是周邊村的村民每天徒步4小時給孤島裡的老人們送吃的。志願者們聽說後,每人每天背著三四十斤的水和食物走山路送去物資,像螞蟻搬傢一樣人力運輸。
“這就是社會力量,”郝南說,“當災後的需求和剛性的投入之間存在缺口時,這部分社會的韌性補上瞭。”
在許多救援人的心裡,繞不開的時間點——或許也是情結——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說,那是中國社會應急力量的志願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內的幾名無線電愛好者成立瞭民間救援組織“青島一七五軍團”,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區支援。

◎ 汶川地震發生的2008年,成為中國志願者元年
那年也是譚花加入愛德基金會的第四年,她在當年7月去四川參與災後重建工作。當地一位村支書告訴他們,地震後,路斷瞭,他們村由於位置偏遠也成瞭孤島。一開始,村民們相互接濟,勉強度日。隨著食物逐漸消耗,整個村子快堅持不下去瞭。
村支書終於撥通瞭鄉鎮書記的電話。對方回他,先撐著。但撐到什麼時候?沒人知道。在絕望日漸加重的煎熬中,村支書在廢墟裡找到一隻收音機。他打開調試瞭一會兒,呲啦的聲波裡傳來總理的聲音:“大傢堅持下去,黨和政府不會放棄你們。”
幾個月後,在建起的臨時板房裡,村支書對譚花他們講起那個時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們村子沒有被放棄,”譚花回憶著,強調道,“社會公眾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作者 王之言 | 編輯 周褶褶
排版 魏蔚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