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面这篇《名利场》的报道,记录了 Vision Pro 在科技评测文章看不到的一面。
从封面就可以看出来不同,低调示人的库克让记者捕捉了他戴上 Vision Pro 的独家形象。
除了库克本人,《名利场》还采访了导演卡梅隆、多位苹果高管。
这些亲自研发产品,或者站在技术前沿的人物,分享了 Vision Pro 的起源、初次使用 Vision Pro 的感受,既不吝啬溢美之词,也谈到了大众槽点。
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甚至人类的未来,他们给出了主观的、充满人文色彩的答案。能否说服我们掏出 3500 美元购买头显,则是他们无法掌控的问题。
划重点
iPod、iPhone 和 Vision Pro 诞生于同一个秘密研发基地。
库克喜欢戴着 Vision Pro 工作、冥想和在天花板上看电影。
从事 VR 行业 18 年的导演卡梅隆认为 Vision Pro 是一次革命、一次宗教般的体验。
Vision Pro 不会带给人像其他 VR 设备那样的「幽闭恐惧」,和现实世界自然地交互,同时数字世界的真实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Vision Pro 的价格、体积和重量、应用生态不完善,都只是暂时的问题,但它可能让我们陷入类似智能手机的技术成瘾。

库克第一次体验 Vision Pro 时,它还没有被正式命名。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大约六七年,甚至八年之前,Apple Park 还未建成。
然而现在,我们就坐在 Apple Park 的圆形大楼里,围坐在一张橡木桌旁。外面刚刚下过雨,云层在松树、柑橘树和枫树之间散开,阳光从草地上的池塘反射出来。库克用他那温和的口音,回忆起那些年前的某一天,他第一次见到 Vision Pro 的情景。
相遇地点是在 Mariani 1,一栋不起眼的、窗户涂黑的低矮建筑,位于前苹果总部。这是苹果的秘密研发基地之一,成千上万名普通员工被多重安全门层层阻隔,永远无法踏足。其中的密室孕育着各种创意产品,比如可折叠的 iPhone、键盘可收缩的 MacBook 和透明电视。它们中的大多数永远留在这栋楼内,存于派力肯防护箱中,安放在加锁的橱柜里。
这座建筑已成传奇,两款改变世界的产品,iPod 和 iPhone,便诞生于此。也是在这里,工业设计团队秘密研发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新设备。当库克走进房间时,Vision 产品组副总裁 Mike Rockwell(迈克·洛克威尔)在那里,听见库克形容它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复杂的装置」。
库克被邀请坐下,一个巨大而笨重的机器被放在他的面前,它粗糙得就像一个巨型盒子,内置了多层屏幕,凸出的摄像头犹如触须。这还不是一款可以穿戴的设备。风扇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电线在地面蔓延,连接到另一个房间的超级计算机。当按钮按下,指示灯亮起,CPU 和 GPU 开始以亿计的频率脉动……这一刻,库克仿佛置身月球。
库克就在月球上。他与阿波罗 11 号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并肩,环视四周,看见黑色星空下古老尘埃的幽灵般荧光。远处是地球,蓝色的小点,所有奇迹的发源地。
同时库克也在那个密室里,那栋秘密建筑里。他可以看到洛克威尔和其他苹果员工,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双手。就在那一刻,库克明白了眼前一切的意义,仿佛宇宙亲口告诉了他什么。这个戴在他头上的粗糙装置将改变所有,是计算、娱乐、应用程序和记忆的未来,是苹果的下一个产品类别。

首批博主开箱.
但库克不知道,他的工程团队如何把一个需要超级计算机、风扇和众多屏幕的设备,缩小为比一盒意面稍重的护目镜。「我不确定具体时间,但我坚信我们会达成这个目标。」
这一刻终于到来。首款 Vision Pro 外观是一个鞋盒大小的白色立方体,周五上市,被数万名苹果粉丝预订。吸引狂热粉丝不难,库克面临的挑战是,让大众相信,值得拿出 3500 美元购买这款空间计算设备。
Vision Pro 长得像黑客帝国的滑雪装备,并且目前还无法使用 Netflix、YouTube 等流行 app。不过,几乎每个在发布前试戴过的人,反馈都非常热烈。
「我想说,几乎是一次宗教般的体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谈到他首次试戴 Vision Pro 时说。他强调自己不是苹果的信徒,但体验确实让他震惊,打消了他最开始的怀疑。
另一位知名电影人乔恩·费沃洛(Jon Favreau)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打动他的,是 Vision Pro 如何改变讲故事的方式。费沃洛甚至专门为苹果创作了内容,展示了 Vision Pro 的 3D 功能,其中一个场景是恐龙从屏幕中爬出,仿佛要将人吞噬,「我很兴奋,这是我之前无法做到的」。

从计算器就开始写技术文章的资深科技记者奥姆·马利克(Om Malik)的评价更加夸张:「令人震惊!太不可思议了!你能感受到宇宙的振动!」
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体验 Vision Pro 的人,无论是投资者(哇!)、设计师(哦!)、分析师(噢!)还是制作人(啊!),都不吝赞美之词。
当我第一次走到乔布斯剧院时,脑海中就回响着他们「哇」「哦」和「啊」的声音。这座圆形建筑的墙壁全由玻璃构成,支撑着似乎悬浮在空中的巨大圆柱形屋顶,致敬梦想家乔布斯,唤起访客对创新精神的敬仰。当一个苹果员工手持午餐盒大小的派力肯盒子走出来时,我心中有了预感,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的,正是那件让所有人兴奋不已的产品。
几个月前,我还对盒子里的东西毫无兴趣。我没看六月的 Vision Pro 发布会,没有深究那些解析产品的博客,也没有理会社交媒体的种种猜测与讨论,就像对待英国王室与哈利、梅根的新闻那样。坐在与库克共同回顾那场发布会的房间内,我坦白了我的冷漠,我看过类似的故事,对于这场表演秀,我似乎已经预见了它的全过程:开头、发展,以及结局。

2013 年,洛杉矶的一间会议室里,我第一次将 Oculus VR 头显戴在头上。确实很酷,我不禁「哇」了出来,在体验一款图形粗糙、像极了毕加索嗑药后设计的游戏时,又忍不住赞叹了几声。但几分钟后,我开始感到有些闷热和不适,到了中场休息时,我甚至陷入了一种焦虑,害怕失去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只能在虚拟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
随后的十年里,尽管图形变得更加细腻、处理器更快,但每当尝试新的 VR 设备时,我总是有同样的感觉。无论是 Rift、Vive、Quest、Quest 2 还是 Quest 3,我都试用过一两次,然后就把它们束之高阁,因为我不想再体验那种戴着面具的压抑。
去年 8 月,我被邀请到苹果洛杉矶的办公室、Beats 曾经的所在地,体验我以为的又一款 VR 设备。我坐在一间装饰着白橡木家具和抛光地板的现代时尚房间里,脑海里想的全是回家得花多久,以及我是否应该走小路,因为那时候的高速简直就是噩梦。
我坐在一张灰色沙发上,一名苹果员工让我伸手去拿 Vision Pro 并戴在头上,我不太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只想尽快了结。接着,如我所料,周围的世界消失了,这是戴上 VR 头显后的常见体验。但几秒钟后,数字帷幕被拉开,真实的世界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看到了自己的手臂和腿,紧接着,苹果应用的图标如同五彩斑斓的幻影浮现。

VR 头显和 Vision Pro 的距离,就像儿童施文自行车与湾流 G800 私人飞机的差别。我回想起了拨弄第一代 iPod 的滚轮,以及双指放大初代 iPhone 图像的新奇感觉。
使用 Vision Pro 时,我只需看向一个图标,并轻轻一拍手指,应用便会启动,如同魔法般悬浮在面前,呈现出我此生所见最清晰的画质。我可以直接用手挥动切换图片,用指尖轻点移动物体,完全不同于其他 VR 设备那样拿着控制器,双手挥舞着像龙虾的爪子。使用 Vision Pro 时,眼睛就像是鼠标。库克听到我的体验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的世界中,但我们享受的内容却是平面的。」

Vision Pro 的交互方式.
通过 Vision Pro 的演示,我仿佛置身于俄勒冈州著名的胡德山层状火山之旁,真实地听到并看到无数雨滴落入镜湖,缺少的只是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我与高清的空中图像进行了互动,用我的手指触碰它们,而非通过鼠标或键盘。我首次体验到了空间,用「惊人」来形容都不为过,仿佛对方就站在你面前,似乎能伸手触及。我观赏的电影片段宽约 30 米,清晰度超过了任何 IMAX 影院。最重要的是,我能看到我周围的世界。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封闭或压抑,没有幽闭恐惧的不适。我就在房间里,同时我无所不在。
那天离开苹果办公室后,我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当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时,这台还算新的设备,突然过时得像从苏联时代发电厂中挖掘出来的遗物。
「你知道吗,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反馈是,等等,给我一点时间。我得消化一下刚才的体验......这多酷啊,有多少次产品体验能让人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是吧?」在 Apple Park 共进午餐时,苹果全球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格雷格·乔斯维亚克(Greg Joswiak)告诉我。

参与第二次体验时,我才真正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洛杉矶的苹果办公室。两位员工引导我到一个房间,我戴上 Vision Pro 后,场景如帷幕拉开,我看到了他们。演示进行到一半时,我下意识地拿起一杯茶喝了一口,就在那一刻,我的一个手指突然出现了短暂的闪烁。
我问道:「等等,我这是怎么了?你们是真实的么?还是说……」
「不,你看到的是实时渲染的我们的。」一名员工解释。
我愣在那儿,一时间无言以对。我本以为自己所见的是现实世界,所有数字化的奇迹只是附加在这个基础之上,Vision Pro 是透明的,仅仅在其表面增加了一层科技效果。然而,真相却恰恰相反。
「这不仅仅是一次进化,这是一次革命。」卡梅隆在听到我的体验后回答。他已经在 VR 领域工作了 18 年。
卡梅隆解释说,Vision Pro 之所以显得如此逼真,是因为它提供了 4K 分辨率的图像。「这就像是把一台 75 英寸电视的画质直接传送到你每只眼睛里——2300 万像素。」
相比之下,一般的 4K 电视屏幕大约只有 800 万像素。苹果工程师们不是简单地从一个 4K 显示屏上裁剪一个小块,而是把双倍以上的像素紧凑地放置进了一个与人眼球大小相当的空间。在卡梅隆看来,这「解决了一切难题」。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技术奇迹,拥有着 2300 万像素,以至于你几乎分不清现实与数字化合成,苹果还有些问题尚未解决。
在硅谷有一个关于乔布斯的传奇故事,发生在约 25 年前的 Mariani 1 大楼,那也是库克多年后首次见到 Vision Pro 原型的地方。
90 年代末,乔布斯带领着一群工程师,他们正努力开发第一代 iPod,突破物理学原理,把它塞进一个尽可能小的盒子里。当无法再缩小时,他们将成果展示给乔布斯,打造原型机已经花了数百万美元。乔布斯仔细看了看,却表示它还需要更小。工程师们回应说已经达到了极限,乔布斯走到一个鱼缸前,毫不犹豫地将原型机扔到里面,水花四溅,原型机沉没,乔布斯指着冒出的气泡说,「看到那些气泡了么?那就证明你们还能让它更小。」
「看,这儿有 M2 芯片...R1 芯片...几乎零延迟...5000 项专利...七年时间。」苹果公司工业设计副总裁理查德·霍沃思(Richard Howarth)用浓重的莱斯特口音说着,他指着我面前摆放的几十个拆卸下来的部件,它们组成了 Vision Pro 的「骨架」。然而,我脑海中浮现了 iPod 的原型,还有一个假设:如果乔布斯还在世,他会不会将 Vision Pro 投入鱼缸,然后指着泡泡说:「看,还能更小!」
人们对于 Vision Pro 普遍有个不满:体积和重量。它重约 20 盎司(约 567 克),这听起来不算太重,但我们通常用盎司来称呼食物的重量,而非我们穿戴的东西。20 盎司相当于五块黄油那么重——想象一下,如果你整天脸上挂着五块黄油,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VR 先驱卡罗琳娜·克鲁兹-内拉(Carolina Cruz-Neira )告诉我,一款设备戴在脸上的感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项技术的接受度。「我研究 VR 技术已经超过 30 年了,只有当我们能够摘掉你脸上笨重的潜水面具,让它变得更加轻便和不显眼,我们才能让这项技术真正走向大众。但体积和重量的问题,不可能在短短一年内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了 Vision Pro 的商业化。苹果公司的高管们表示,「我们对目前的销售情况感到兴奋」,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认为,预售首周末大约售出了 18 万台。摩根士丹利预测,接下来的五年内,销量将增至每年 200 万至 400 万台,Vision Pro 将成为苹果的一个新产品类别。一位我咨询的高级分析师甚至认为,几年后 Vision Pro 会像太阳镜那样流行,售价将低于 1500 美元。但也有分析师如郭明錤,认为这款产品在一段时间内仍旧是一个小众产品。
我本来不打算询问霍沃思关于重量的问题,但他自己主动提了起来。向我说明哪些部件是由镁、碳纤维和铝制成时,他顺便提到了重量,强调这些都是地球上最轻的材料,没有更好的替代品了。「我们无法让它更轻或更小了,这已经是技术的最新成果。」
我在苹果遇到的其他人也有相似的看法,比如苹果全球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格雷格·乔斯维亚克 (Greg Joswiak) :「感觉就像我们伸手进了未来,拿回了这款产品,把未来戴在了你的脸上。」洛克威尔也说:「我们在这么小的外形中融入了尽可能多的技术。」
「你甚至可以躺在沙发上,把屏幕投影到天花板上。」库克告诉我,他在天花板上看了体育喜剧《泰德·拉索》的第三季,还建议我用 Vision Pro 冥想和提高工作效率。当我回家连接上 Vision Pro 后,我也在天花板上观看了《福特大战法拉利》,空间音频让我感觉福特 GT40 就在房间里驰骋。
用 Vision Pro 的虚拟键盘打字,就像用脚趾夹着笔写字,并非不可能,但不太现实。不过当我戴着 Vision Pro 打开我的 MacBook Pro 时,屏幕融入了我的 AR 视野,我可以非常流畅地工作。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就是我通过 MacBook 用 Vision Pro 写下的,如果你现在能看见我,你一定会觉得我看起来像是《少数派报告》里的汤姆·克鲁斯,可能还要帅那么一点点。

当然,还有那些空间效果,我已经录制并观看了很多空间,记录下孩子们的玩耍和聊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在回放时让人沉浸在情感的洪流之中,宛如走进了一个生动且真实的记忆世界。我想再强调一遍,逼真程度真的很难用言语形容,我偶尔会回到镜湖,关闭所有的通知,只是静静地坐在湖边,享受 5 到 10 分钟的宁静,聆听雨声,然后再重新投入工作。
不过,使用过程也会出现一些意外。当你在一个房间里用 Vision Pro,然后走到另一个房间继续打开同一个应用,你得四处寻找它。有时候它会出现在天花板上或是地板上。有一天我找不到我的短信应用,转身一看,发现它竟然出现在我的浴室里。后来我才知道,长按设备上的数字旋钮几秒就可以重置应用。

过去两周里,我越用 Vision Pro 越多,也就越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重量和体积,每一代产品都会改进,更不是担心它会让人孤独地消费内容,已经有近一半的美国人独自看电视了。至于像 Meta、Netflix、Spotify 和 Google 等科技巨头目前还没有为这款设备开发应用,也并不构成问题。一旦消费者群体稳固,内容创作者可能会改变态度,迪士尼提供了包括《星球大战》和漫威系列在内的 150 部 3D 电影。甚至连价格也不是问题,因为苹果要是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补贴 Vision Pro 的成本。这对于苹果财务的影响,相当于库克不小心在沙发缝隙里掉了一枚硬币。
我关注的是一个似乎无解的问题。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 Apple Park 的地下办公室。我在那里观看了一次演示,场景是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我仿佛坐在那个干燥的沙漠地貌中。我玩了水果忍者,用双手在空中挥动切割水果。然后我尝试了一个 DJ 应用,一个虚拟的转盘在我面前出现,我可以滑动音量条、调节混音器、刮擦唱片。我还召唤了一个挂在天花板上的迪斯科球,周围有动画人物随着音乐跳舞。
我的 DJ 表演进行到一半时,一位苹果员工说是时候结束了。当我摘下 Vision Pro 时,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种情况在家里又发生了,滚动浏览过去几周我为孩子们拍摄的空间,他们好像真的就在我面前。几分钟后,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我面前的 Word 文档就会关闭,IMAX 屏幕也会消失。

每当我摘下设备,其他所有的设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趣:75 英寸 OLED 电视变成 90 年代的 CRT 电视,iPhone 是过时的翻盖手机,甚至周围的真实世界也显得异常平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就像我无法想象开车时没有音响、没有手机无法与人交流或给孩子拍照、没有电脑就无法工作一样,我可以预见,总有一天,我们将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 AR。当技术越来越多地包围我们,我们可能会像需要药物一样渴望 AR 能带来的多巴胺刺激,就像今天我们和 iPhone 的关系。
Vision Pro 的沉浸感太强了,但我真的很想通过它和世界交互。一位硅谷投资者对我说:「我确信这项技术很出色。但我仍然认为,也希望它不会成功。苹果现在越来越像是一个打着康复服务幌子的高科技成瘾产品贩子。」这话听起来很严肃,但他提出到了我们大家都有的感受——成为智能手机的奴隶。他看过这样的情节发展,知道故事的起始,也知道接下来的发展,甚至知道最后的结局。

我没来得及问库克这个问题,但我问过他,科技是否发展得太快了,AI、空间计算以及我们对技术的依赖是否过多了。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问。
「我认为很难准确预测。」他回答。
「但是你正在塑造它,对吧?你难道不能预测吗?」
「我们所做的就是保持兴奋,然后拉动绳子,看它会引领我们去哪里。是的,我们有路线图,也有明确的想法,但很多时候也是在摸索和探险。有时候点与点会连接在一起,然后引领你去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乔布斯也说过:dots will connect。
问题是,我们即将进入的空间计算时代,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它将成为下一个必需的技术,让我们无法生活在没有增强现实的世界中?
我认为格雷格·乔斯维亚克的话说对了一半。他说「你正在把未来戴在脸上」,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是苹果正在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走向一个新的计算时代。有些人正在拼命追赶,而其他人则被拖着走并大声抗议。但我们都在前进。我们正走向月球,我们将环顾四周,看到黑色星空下古老尘埃的幽灵般荧光。我们将知道这就是计算、娱乐、应用程序和记忆的未来,这个戴在我们头上的装置将改变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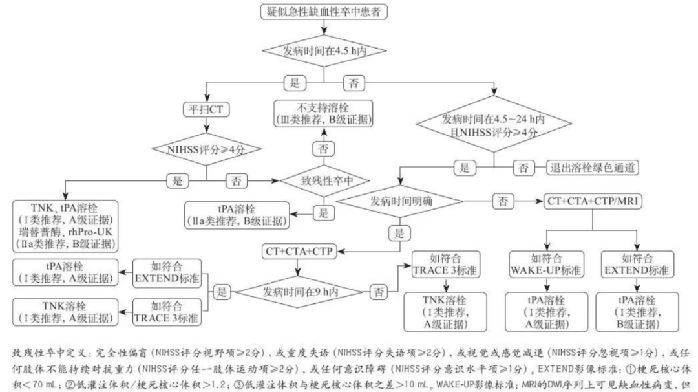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