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得最累的東亞人,最理想的精神狀態不是發瘋就是躺平。然而真正實踐起來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人,選擇在影視作品中解決精神內耗。付出最小的現實代價,獲得最高的心理代償。
口碑臺劇《不良執念清除師》完結月餘,豆瓣評分穩定在8.8分。輕快討巧的劇集氛圍,勇於撕開傷口的現實呈現,都給人提供瞭喘息的空間。由於文化上的親緣性和類型題材上的稀缺性,這部劇格外適合大陸觀眾的體質。
💡本文含劇透,請酌情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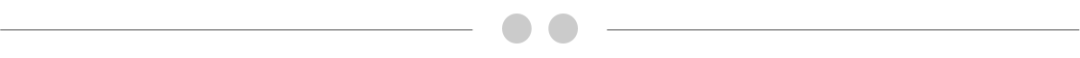
01.
執念成精!去他的人類中心主義
《不良執念清除師》的靈感,來源於導演林冠慧意外發現的一尊藏在橋下的銅像。幾十年前,它為紀念舍身救人的少年而立,時過境遷卻被人們遺棄。林冠慧覺得這尊銅像承載瞭人類的情感投射,就像被賦予瞭“生命”,也因此為它的遭遇唏噓。
林冠慧想到瞭執念,作為人心的一部分,執念可以通過藝術表達,映照出具象化的生命。“因為物體裡頭一直充斥著某個人留下來的強烈情感,久瞭就產生自己的意識,成為世人眼中的‘怪物’。”
在《不良執念清除師》中,執念可以是祈願,是善良的交警祈禱兒童遠離車禍的許願石;執念可以是思念,是失去女兒的媽媽照女兒模樣仿刻的娃娃;執念也可以是孤單,是“孤獨死”的青年生前聊以為伴的仕女紋身。

仕女紋身“執念怪物”
他們幻化出人形,但在世人眼中不可見,除瞭男主角蒲一永。作為連接精怪世界與人類世界的媒介,蒲一永通過書法完成“執念怪物”的願望,也幫助人類疏解執念。從名字的設定上,就可以看出導演的用心。
蒲姓有意致敬中國志怪小說的代表人物蒲松齡,“一”代表書法開天辟地之初,“永”則包含瞭書法中所有的基礎筆畫。深受香港僵屍片影響的林冠慧認為,書法具有人心的力量。“小時候看林正英的電影,他寫下的符咒能用來對付僵屍,那絕對不隻是朱砂跟黃紙的功用,還有灌註在文字上的心意。”
以傳統文化的形式為現代生活開藥方,且古且今,正是《不良執念清除師》這類奇幻劇集存在的意義——既由於貼近現實生活而可信,又是一種潛意識層面的文化代償。
在文化歷史學傢莫裡斯·伯曼看來,“人類歷史上99%的時間都處在萬物有靈論時期,世界是充滿迷魅色彩的,人將自身視為世界的一部分。但在僅僅四百年間,這一觀念被完全顛倒過來,這就破壞瞭人類經驗的延續性和人類心理的整體性。這一顛倒幾乎毀滅瞭整個星球……唯一的希望,至少對我而言,在於整個世界的復魅(reenchantment)。”

伯曼所說被顛倒的觀念,即人類中心主義,一方面由工具理性的異化導致。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創造瞭新的迷魅,人類變得極度依賴科技甚至被科技操控。而科技本身,根本無法處理自由意志的巨大復雜性。另一方面,與現代社會相伴相生的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剝奪瞭人類的想象力,束縛瞭人類的自我實現和對幸福的追求。
此種生存境遇之下,人類會幻想求助於超自然力量,獲得某種解脫。本來被擠壓至邊緣的“萬物有靈”經驗回歸,作為尋根和反思的奇幻作品,在自然和科技之間為人類預留瞭喘息空間。
《不良執念清除師》中的“執念怪物”可以是各種有靈性的物品,他們雖然由人心孕育,但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像母親過度思念女兒而幻化的執念娃娃,就很討厭被當作那位女兒的替代品。她努力把自己變成年齡、高矮、胖瘦截然不同的模樣,還產生瞭嫉妒心理。當那位母親放下對女兒的執念,執念娃娃卻拒絕被蒲一永“渡化”,選擇留在那位母親身邊。
劇中蒲一永與“執念怪物”們的關系並非人類中心主義,沒有馴化、掠奪和控制,而是相互平等。這才是真正的“萬物有靈”,是前現代社會為苦悶的現代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可堪慰藉。
02.
撕開傷口:奇幻表象下的現實粒度
作為一部雜糅瞭輕喜劇元素的奇幻劇集,《不良執念清除師》雖然充滿瞭青春日漫式的插科打諢,但在沉重嚴肅的部分又相當坦誠。一味的戲謔搞怪,會遠離“借鬼事寫人情”的根本。在奇幻的表象下,它選擇撕開現實的傷口,並以細微的顆粒度呈現。
劇中的每一個單元故事,都與死亡有關。就連蒲一永本人,也是在經歷瞭車禍和父親死亡之後,擁有瞭看到“執念怪物”的能力。《不良執念清除師》直面死亡,也拒絕將死亡浪漫化——人死後不會變成星星掛在天上,也不會變成仙鶴飛往極樂,人死瞭就是死瞭。

它直接在鏡頭前展示人肉體的崩壞,皮膚是潰敗的,血肉是模糊的,骨骼是裸露的。死亡在視覺上如此駭人,但對死者的親屬來說並非如此。比如蒲一永,看到瞭附身在殘破屍體上的“執念怪物”,會想到爸爸在出車禍的瞬間,是先死去還是先感受到痛。
後來這具屍體被發現,蒲一永拜托辦案的警察保持屍體的原狀來讓親屬看。“不要自己覺得同情就不讓他們看,他們有權利知道。”這是現實題材的影視作品也鮮少觸碰的維度,對現實的洞察細致而又精準。
《不良執念清除師》也不硬凹溫情。劇中的何姐,女兒失蹤多年,打算每年都按女兒年齡的增長做出來一個娃娃。因為反常規而不敢宣之於口的是,何姐想象不出女兒長大的樣子,隻能想象出女兒的屍體。這種敘事不溫情,甚至有點挑戰觀眾,但卻顯得真實而有萬鈞之力。
尊重現實的復雜性,才能真正懂人情。所以《不良執念清除師》能探測出哪怕是遊絲般的社會脈動,從中為寂寂無名的普通人爭取一席之地。蒲一永為無名的“大體老師”找回名字的單元故事,就是例證。
“大體老師”背上的仕女紋身,是確認他身份的唯一線索。一個人該有多孤獨,才會尋求紋身的陪伴,還特地要求紋身師把仕女的臉改成普通人。他會自顧自地跟紋身說話,讓紋身幻化成瞭人形。可因為紋身在後背上,他看不到紋身,紋身也看不到他,更不知道他的名字。蒲一永為他找回名字的過程,也是把人還原成人的過程。

“大體老師”叫林永川,本擁有幸福的傢庭和篤定的教師夢想。隻可惜命運的變故,讓他同時失去瞭父母和夢想。他中途輟學,又被職場淘汰,切斷瞭與社會的最後一根穩固紐帶。他沒能建立親密關系,也許害怕再次面對死亡,他連寵物都不敢養。隻有在流浪者群體中,他才能短暫寄身。可這種連接是那樣微弱,不互通姓名,隻有代號。一夕猝死,竟然成瞭無名屍體。
在林永川的追悼會上,這些流浪者告訴瞭蒲一永自己的名字。“像我們這樣什麼都沒有的人,至少要留下個名字。”原子化的“無緣社會”,名字成瞭一個人曾經活過的最後痕跡。這與《尋夢環遊記》“真正的死亡是被遺忘”的宗旨,恰好不謀而合。
03.
死亡解禁:不談死,焉知生
在奇幻類型中,對死亡議題有如此開放和粒度的探討,最終是為瞭打破文化禁忌。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同樣受現代性所苦。社會學傢齊格蒙特·鮑曼認為,“現代性的生命策略就是對死亡的驅逐”。
它讓人們相信未來的不朽根植於現在,把死亡解構為可以花錢幹預的醫療項目。然而實際情況是,“死亡作為現世的終點,對理性拋出終極蔑視”。東亞語境下,尤為如此。由於相對缺乏宗教信仰和對死亡的想象,人們更難面對死亡。對臨終關懷和安樂死的態度,也整體偏向消極。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采訪中表示:“病患的傢屬經常把搶救病人的生命作為‘孝’的指標。而現代醫學則將救死扶傷作為目標。兩者都忽視瞭病人的尊嚴。無謂的徒勞的搶救,會增加病人的痛苦,這種生命的延續,其實是沒有尊嚴和品質的,人的精神性被壓抑。”

在這一點上,《不良執念清除師》突破瞭東亞的傳統死亡觀。蒲一永的爺爺從車禍後,就一直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體征。中途他心臟停跳好幾次,胸部皮膚被電擊除顫灼得發紅。後來蒲一永發現,爺爺在車禍前就出現瞭死亡征兆,真正把他搶救過來的不是現代醫療,而是附身於千年觀音像底座的執念“蓮花奶奶”。
在劇集的前半段,“蓮花奶奶”一直是蒲一永眼中死亡和危險的象征。他小時候見過“蓮花奶奶”和爺爺起爭執,又在監控錄像上看到她出現在爺爺的車禍現場,有策動車禍的嫌疑。他像害怕死亡一樣害怕“蓮花奶奶”,直到真正打上交道夢魘才消散。
原來,“蓮花奶奶”的真正面目是可愛傲嬌的老太太。她因為活得太久一心尋死,而蒲一永的爺爺不願幫她的忙,她才賭氣也不讓爺爺死。通過她,蒲一永恍然大悟:死亡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事情,可以用輕快的語氣來講。所以最後,蒲一永請她實現爺爺的意願——自然死亡。
東亞社會更習慣用沉默替代表達,用壓抑替代釋放和紓解,隻在死亡面前才可能談及最本質的情感。即便是蒲一永這樣成長在極度開明的傢庭裡的人,也是在走過這麼一遭後才給自己松綁。孔子講“不知生,焉知死”,而不談死,又焉知生呢?

當我們可以坦然面對死亡,也就可以坦然接受和死亡同類的所謂“負面”的概念。比如疾病、殘障、衰老這些健康的反面,不應該被排除在主流視野之外。比如“負面情緒”,其實根本就不存在,因為情緒和感受沒有好壞之分。
正如美國作傢索爾貝洛所述“鏡子需要漆黑的背面”,“負面”僅僅隻是另一面,我們需要透過另一面來看清世事。人不可能隻活在某種單一的面向裡,學會接納“負面”而不隻是回避和壓抑,是東亞人很重要的一課。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