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吞吞
「『女婿』在中國病人醫療護理整個流程當中發揮著巨大的價值。」
這是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胸外科主治醫師王興研究出的「女婿經濟學」。
9 年前,王興的丈母娘檢出胃癌,從腫瘤醫生變成癌癥患者傢屬,他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認為「女婿們」有能力解決在醫療過程中面臨的一切困難。
從醫十餘年,在悲歡離合濃度最高的腫瘤病房,王興觀察著來來往往的癌癥傢庭,他覺得看病最復雜的,是在傢庭內部捋順細枝末節的小問題。
他把這些發現和思考寫成書,陸續有人慕名而來,一手拿著掛號單找他看病,一手拿著新書找他簽名。而王興隻是擺擺手,「觸動歸觸動,技術歸技術,看病還是推薦你去找我們主任」。
以下是王興的自述。
成為癌癥患者傢屬後,研究出「女婿經濟學」
2014 年,我正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進行住院醫師輪轉。下瞭手術打開儲物櫃,手機上赫然有 10 多個老婆(當時還是未婚妻)的未接來電,當時隱隱有些不太好的預感,再打回去,就得知丈母娘檢查出胃癌。
我是一個腫瘤醫生,和胃癌病人打交道是一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工作,直到這個「病人」是我自己的傢人。
約定的婚期就在兩個月後,突如其來的癌癥讓傢裡一下子進入非常混亂的狀態。我們一邊籌辦婚禮,一邊帶丈母娘看病、聯系手術。當時既擔心丈母娘不能順利參加我們的婚禮,又擔心婚禮上她要是情緒激動,會進一步影響病情。
幸運的是,找到瞭專傢做手術,手術過程也十分順利。我們默契地瞞住瞭丈母娘,她始終以為自己是腫瘤病房裡唯一的良性患者。
出院那天,傢人去辦理手續,出院小結就交到瞭獨自留在病房的丈母娘手裡。診斷書上的胃癌二字,讓她一下子就崩潰瞭。而我,也毫不意外地挨瞭老婆一頓罵,責怪我沒有和病房裡的醫生做好鋪墊。
癌癥讓人變得非常敏感。尤其是當你看到一直堅強、勇敢的父母,面對自己的疾病六神無主的時候,真的會很心疼。

手術後,我們面臨化療方案的選擇。其中一種藥為奧沙利鉑,國產的奧沙利鉑,一個周期(3 周)大約需要 1500 元;進口的則約為 15000 元。而權威期刊發表的論文證實,國產仿制藥無論是效果上還是副作用上,都不比進口藥差。
那時我的工資一個月也不到 15000 元,從一個醫生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國產藥完全夠用。但這不是我的病人,而是我的丈母娘,要是真選瞭國產藥,也擔心有閑言碎語指責我不孝順、不盡心、摳門、不是親媽等等。所以最終,我還是選擇瞭進口藥。
也是這段經歷讓我意識到,當癌癥的消息傳來,傢庭裡非常需要有一個人能夠做出決斷。在愛意和痛苦都洶湧泛濫的時候,有人要拾起那些關於治療周期、副作用、經濟成本的思考,做出一些理性甚至冰冷的決定。
服用化療藥後,丈母娘出現瞭嚴重的副作用。一方面想減輕一些她的痛苦,另一方面這也僅是輔助化療,於是我拍板決定不再化療。同時,也意味著停藥後萬一癌癥不幸復發,我要承擔全傢人的指責。不過萬幸的是,丈母娘現在一切安好。

當癌癥來臨的時候,大傢都不知道這艘船會往哪裡走,就需要有人來掌舵。在我的傢庭裡,擁有醫學知識、又相對能保持客觀理性,作為「女婿」的我是相對來說最適合做決策的那個人。以我自己為觀察對象,我提出「女婿經濟學」,認為「女婿」在中國病人醫療護理整個流程當中發揮著巨大的價值。
但這隻是打引號的「女婿」。我也遇到過患乳腺癌的婆婆,把治療方案的選擇全權交給兒媳做決定。這個決策者可能是女兒、兒子、母親、父親或傢庭中的其他人,關鍵不在於性別或身份,而是這個人能夠獲得傢庭大多數成員的信任、做出合理的決策,同時,萬一不幸出現瞭不好的結果,還要能夠挨罵。
在臨床上談話的時候,我發現每個傢庭最終都會通過外部或者內部的壓力,「憋」出這麼一個人來。也因此,我寫瞭《病人傢屬,請來一下》這本書,想告訴那些可能剛被推上決策者之位,還有點無措的癌癥患者傢屬:沒關系,不要著急,我是這樣過來的,你也可以。
繞不開的談錢
我自己還是醫學生的時候,並不能理解那些醫生們為什麼談方案前先問患者經濟情況。在當時的我看來,治療方案不應該因為錢的因素而隨意改變。
直到我也開始獨立出門診。當時第三代靶向治療的相關研究有瞭新進展,有個肺癌晚期的病人可以選擇靶向治療,我就把這個方案告訴瞭病人和傢屬。
病人沒有直接回答,但傢屬非常激動,覺得看到瞭希望,表示一定要給父親用最好的藥。但當我告訴他這個方案每個月需要三萬塊的時候,傢屬陷入瞭沉默。他幾乎是哭著告訴我,他一個月最多隻能夠掙到七八千。
後來,如果我知道患者傢庭困難,我不會再告訴他們世界上又出瞭什麼最新的治療方法或昂貴的新藥,我隻會向他們介紹最符合他們經濟實力、治療效果也差不多的方案。這樣的方式,雖然可能一定程度上違背瞭患者的知情同意權,但對傢屬來說是一種安慰,他們會覺得,「是醫生為我選擇瞭一個合適的方案,不是我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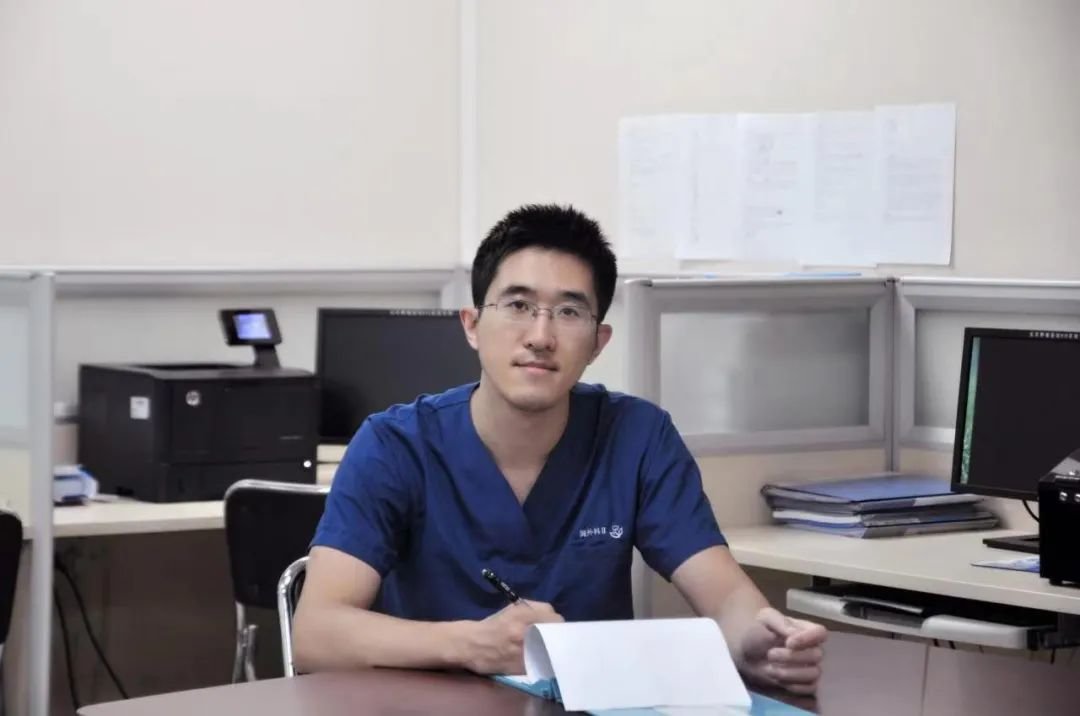
有時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切入口。
一次我和傢屬談話,傢屬問我術後化療是進口藥好,還是國產藥好,我如實告訴她從療效上來看沒有非常大的差別。她來回打瞭好多個電話,糾結瞭很久,最後告訴我他們還是用進口的。
我說好,但是進口藥需要走個流程,大概要三個工作日後才能使用。
然後發現傢屬一下子變得很松弛,像找到稻草的感覺,她說「進口的慢是吧?國產的是不是快?那我們要用快的。」
她很巧妙地把用藥選貴的還是便宜的這個問題,轉換成快還是慢的問題。這對我也是很大的觸動,找到瞭一種新的溝通方法。尤其是在經濟上可能有困難的傢庭,我會提供更多信息,而不是單純推給傢屬做一個貴還是便宜的選擇。
看見癌癥傢庭的 B 面
我曾在病房遇到一個患者傢屬舉著手機錄視頻,說有事要找我們醫生問清楚,當時氛圍一下子有點劍拔弩張。
問瞭情況之後才知道,他的媽媽在我們科室做手術,主刀醫生把手術直播的鏈接發到瞭朋友圈。傢屬在直播裡發現,這臺手術實際上一共有 6 個主任上臺,和術前談話說的不一樣。傢屬懷疑其中可能有些問題,所以一急之下直接找瞭過來。
為瞭能幫患者多保留一塊組織,這臺手術較為復雜,我們請來瞭頭頸、胸外、骨科等相關科室的主任一起上臺。但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告訴病人,不想增加他們的壓力,也擔心被誤會成是來索要紅包。
既然傢屬來問瞭,我就認真地和他解釋瞭手術情況。傢屬的態度馬上軟和下來瞭,甚至還有點不好意思。可以感受到,他不是想要來鬧事,他就是很害怕。他在大城市舉目無親,相信你,所以才找你做這個手術,但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手術被直播,又在直播裡發現瞭很多他不知道的細節,他也會擔心,醫生會不會害我的傢人?

癌癥傢庭,每個人的神經似乎都很緊繃。
幾年前,我收到瞭讀者抗抗的一封長信。她的父親罹患胃癌晚期,她終日焦灼不安,在信中說:「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癌癥,它一瞬間擊垮瞭我所有的理智」。在回信中,我給她科普瞭癌癥、安慰她如何以更平穩的心態面對傢人。
從抗抗告訴我的信息裡,我大致瞭解瞭她父親的病情,以及當地醫院給出的化療方案。晚期的癌癥,指南不允許手術,僅僅是化療方案的差別。而化療方案主要根據各項檢查報告的結果制定,給病人查體不會對治療策略造成任何的變化。也因此,我在回信中建議抗抗,如果希望二次確認診療方案,可以帶著父親的全套資料前往大醫院就診,不需要帶著病人親自奔波。
但她並沒有聽從我的建議,還是帶著父親前往上海求診。在途中抗抗的父親突發意外,凌晨送入急診搶救。
像她這樣的傢屬,我在臨床上也見過不少。一聽說傢裡有人得病,就不管不顧,幾乎失去理智。所有「好的」、「可能有用的」,都要去做,害怕不夠盡心、害怕失去、也害怕留下遺憾。
在回信中讀到這段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要教育她,甚至還有些生氣。我已經事無巨細地交代瞭,但她依然沒有按照我說的做,那我會覺得,既然不相信我,還來找我幹嘛呢?
現在想起來,這是我作為醫生不該有的傲慢,我似乎隻考慮瞭作為「病例」的病人,滿心滿眼隻有如何治療,認為病人應該完全相信我並按照我說的去做。但我卻沒有想過,病人為瞭治療付出怎樣的代價、病人的傢庭陷入什麼樣的境地。
如果沒有抗抗的這些信,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那些坐在我面前和我隻有幾分鐘緣分,甚至說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夫你好好給我爸看看」的姑娘,到底都經歷瞭什麼。
醫患溝通不應該是自上而下的教育,而是我們和病人都在同一條船上。
策劃:yuu.|監制:gyou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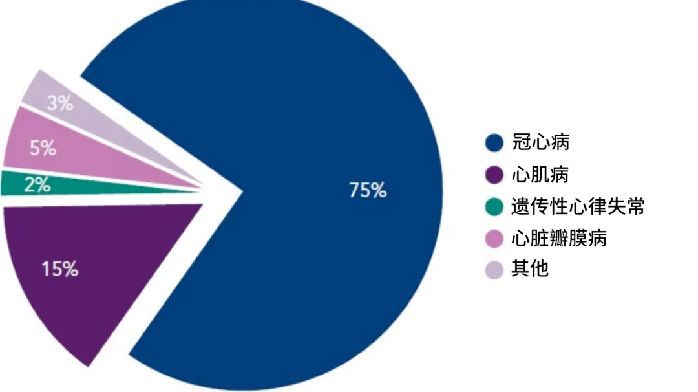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