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視域下的“魔幻現實主義”》
[哥倫比亞] 關滄海(John Gualteros)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3年
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一位哥倫比亞學者用漢語寫作的學術著作,系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關滄海(John Gualteros)博士根據自己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對習慣於通過譯著閱讀外國學者著作的中國讀者而言,這種體驗並不多見。這也是我作為關滄海的博士導師,在北大出版社編輯的堅邀之下,最終打破自己從不給學生與朋友寫序的慣例,向同行和讀者推介這部著作的原因。 1980年代的中國作傢,幾乎無一例外接受過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百年孤獨》的著名開篇——“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裡亞諾·佈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一時間變成瞭打開中國文學寶藏之門的阿裡巴巴咒語,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作傢仿寫、復制與挪用。《百年孤獨》及其代表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神奇魔力也因此引發瞭包括作傢、批評傢與文學史傢在內的中國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的持續關註。在眾多相關研究成果中,關滄海的這部《全球視域下的“魔幻現實主義”》,在一系列已成中國學界共識的問題上提出新的見解,為國內外學術界理解“魔幻現實主義”,提供瞭一種難能可貴的全球視角。

[哥倫比亞] 加西亞·馬爾克斯 (1927-2014)
在本書的後記中,關滄海回憶瞭我當年建議他以“魔幻現實主義”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的過程。取瞭一個地道中國名字的關滄海並不是擁有哥倫比亞國籍的華人,而是哥倫比亞的原住民,他甚至還是馬爾克斯的校友。在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之前,關滄海不僅在馬爾克斯的母校哥倫比亞國立大學獲得瞭西班牙語與古典語言學學士學位,隨後又獲得瞭文學研究和拉丁美洲文學專業的碩士學位,還獲得瞭中國復旦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學位。通過相關課程,關滄海接觸瞭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現代化理論、“第三世界”政治理論、西方與“第三世界”關系、新殖民主義、世界革命和民族獨立進程等方面的知識。 這一中國學者很難具備的族裔背景、學術經歷與知識結構,使他成為研究馬爾克斯乃至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不二人選。盡管在潛意識深處,我一直對美國學者何偉亞在《懷柔遠人》一書中表達的一個觀點深表認同:“生在某一國並說那一國的語言並不意味著對當地之過去有著特許的接近能力。”但我仍然控制不住從事這種跨文化研究時很難克服的樸素的(其實常常是膚淺和沒有道理的)好奇。

《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
[美] 何偉亞 著;鄧常春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10
關滄海出色地完成瞭他的工作。他不僅回應瞭中國學者的關註,更重要的是,他展示瞭與中國學者不同的問題意識。在本書中,按照博士論文的寫作慣例,關滄海總結瞭他寫作這篇博士論文時采用的研究方法,分別是“比較文學”“知識考古學”與“政治無意識”。這種方法論的自覺,使得關滄海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認知從一開始就拉開瞭與中國學者的距離。即,在關滄海的視域中,“魔幻現實主義”並非隻是一種影響瞭中國當代文學的“拉美文學”思潮。對他而言,“魔幻現實主義”恰恰是一個“西方文學”概念。 關滄海從德國評論傢、歷史學傢弗朗茨·羅(Franz Roh)1925年首次提出“魔幻現實主義”一詞開始,追根溯源,勾勒出“魔幻現實主義”的起源、發展和流變,尤其是厘清瞭“魔幻現實主義”與同時期的歐洲三個藝術先鋒派運動——德國“魔幻現實主義”、意大利“魔幻現實主義”以及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內在關聯。顯然,“魔幻現實主義”在關滄海的視域中,是一個更接近於“現代主義”的范疇。他是在現代性的內部,而不是像許多研究者那樣,僅僅將其視為作為地理概念的“拉丁美洲”這一空洞抽象的本質化概念的表征。 關滄海對“魔幻現實主義”的評論,讓人聯想到英國詩人奧登 1941年對卡夫卡的評價:“如果要舉出一個作傢,他與我們時代的關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與他們時代的關系,那麼,卡夫卡是首先會想到的名字。…………卡夫卡之所以對我們重要,是因為他的困惑,亦即現代人的困惑。”奧登的句式同樣可以用於描述流行於1980年代的“魔幻現實主義”。在這一視域中,馬爾克斯作品所表達的“魔幻感”,就不隻是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獨”,而是彌漫於包括中國在內的20世紀末期的“全球視域”的“現代人的困惑”。 關滄海的看法,與中國“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傢韓少功表達過的一個觀點極為近似。2004年,在接受一次有關“尋根文學”起源的訪談時,韓少功斷然否認當年宣告“尋根文學”誕生的“杭州會議”上有過拉美文學熱,他甚至否認會議之前有任何作傢看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韓少功這一讓許多同時代的學者覺得不可思議的觀點,竟然在很多年後關滄海的論述中,得到瞭有力的背書。 換言之,關滄海將“魔幻現實主義”視為20世紀在歐美、拉丁美洲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的一種世界性思潮。在關滄海看來,盡管“魔幻現實主義”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中表現為不同的形式,但它們的共同主題,是不同文明對全球化的最新應答,用他的話來說,“‘魔幻現實主義’揭示出現代性進程的本質矛盾,即‘現代’對人類心靈非理性元素的壓迫”。關滄海認為,“魔幻現實主義”嘗試通過改變知識規則來取消理性的合法性。與福柯的“知識考古/譜系學”一致,關滄海強調權力和話語的互文性,他認為一種話語總是通過建構其他話語的“他者性”來確立自身的認同。拉丁美洲作傢把拉美文化這種歐洲文化的“他者性”(otherness)當成一種新的拉丁美洲身份,使得“魔幻現實主義”概念發生瞭重大的改變。如果說在18世紀和19世紀,被理性霸權批判的拉丁美洲的“他者性”是一種落後的表現,20世紀的拉美作傢則通過“魔幻現實主義”將這種“他者性”轉換成一種激進的文學形式。即,20世紀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在創造瞭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媒介的同時,還創造瞭一種新的拉丁美洲的身份認同(identity)。 對關滄海而言,對“魔幻現實主義”這一概念展開知識考古,對瞭解這一概念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尤其是對於瞭解和認知全球化乃至殖民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包括“非西方”的“西方性”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關滄海顯然不認可批評傢以一種本質化的“非西方性”或“反西方性”來定義“魔幻現實主義”。他的思想軌跡,明顯打下瞭福柯等西方後結構主義乃至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印跡。與強調原生態或“原初性”本身就包含瞭未被西方污染的自然本質,即本身包含瞭非西方對帝國主義的文化與政治反抗不同,亦不同於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以文學語言講述的拉美數百年來被西方欺凌和掠奪的辛酸史,在薩義德那裡,包括東方(當然也應當包括拉美)在內的“非西方”本身就是一個西方創造與發明的范疇,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他者”,“西方”無法確認自己的主體性。在這一意義上,強調西方與非西方的政治對抗,即在“西方”建立的這種以“東方學”或“東方主義”為名的二元框架中展開非西方對西方的反抗,不僅不可能終結西方觀念、思想以及背後的權力對全球的宰制,反而隻可能導致一個後果,那就是強化這種不合理的權力結構。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烏拉圭]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著
王玫 等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
或許對關滄海而言,對“拉美性”的解構,並不需要薩義德式的這種在“東方”與“西方”、“特殊性”與“普遍性”、“主體”與“他者”之間展開的繁復的理論辯證。一個為我們習焉不察的事實是,包括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在內的所有的拉美文學采用的寫作語言其實並非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使用的“原初”語言,而是屬於歐洲拉丁語系的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這也正是作為現代政治地理概念的“拉丁美洲”的由來。如果我們假設拉美作傢正在通過“魔幻現實主義”來展開對美國與歐洲的文學反抗與政治反抗,這些作傢用於反抗的語言恰恰是西方殖民者的語言。在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傢園”的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當將拉美文學視為“西方的文學”,而不是與西方文學完全絕緣乃至勢不兩立的“第三世界文學”。其實認識到這一點,並不需要特殊的理解力。因為無論是“文學”還是“政治”,對西方反抗最激烈的思想,其實一直來自於“西方”的內部,無論是“文學”中作為20世紀文學主潮的“現代主義”,還是現代西方思想中最傑出的政治遺產“馬克思主義”,概莫如此。 墨西哥歷史學傢恩裡克·克勞澤就曾在《救贖者》一書中尖銳地指出,所謂的“拉美文化”說到底其實就是中世紀伊比利亞半島文化的延伸。近600年來,拉美社會的內在精神秩序的基石始終是來自歐洲中世紀的“君主制和教會,劍與十字架”。拉美“文學爆炸”的四位大師——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富恩特斯、科塔薩爾不僅頻繁旅居歐洲,甚至長期生活在巴黎、馬德裡這樣的西方文化之都,卡彭鐵爾光在法國就生活瞭九年。正如關滄海講述的:“與卡彭鐵爾和阿斯圖裡亞斯一樣,‘超現實主義’也改變瞭彼特裡認識和描述拉丁美洲‘現實’的方式。‘超現實主義’激發瞭他尋找拉丁美洲文化的魔幻元素的欲望,讓他開始進行文學創作的實驗。”馬爾克斯亦從不諱言自己對卡夫卡、福克納的繼承。這些拉美作傢是在歐洲,或者說是在歐洲的知識中,“發現”瞭“自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發明”瞭“拉美”。 因此,在關滄海看來,即使是比“拉美文學”更具歷史感的“第三世界文學”,亦應作如是觀。一方面,兼具“實在”“想象”與“象征”等多重意義的“第三世界文學”作為西方文學的“他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批判與解放的功能,另一方面,“第三世界文學”被符號化的特質,譬如那種通常被用於進行文學反抗的方式——作傢創造與發明出的屬於特定文化傳統的“浪漫”或“懷舊”,又使其在無意識中不斷返歸西方文學,成為世界文學——西方文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傳統的發明”歷來就是西方普遍主義乃至殖民主義的題中之義。基於這一理解,如何面對兩種看起來互為鏡像的文學,乃至文化政治在“現實”與“虛構”層面的辯證互動,就成為在我們解讀“魔幻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乃至“第三世界文學”這些現代性范疇時,很難在一種我們熟悉的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展開的原因。 如果說關滄海對“魔幻現實主義”的“拉美性”的解構帶有明顯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印跡,那麼,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理論對他的影響則更進一步表現為對“文學性”的反思與批評。與拉美同行不同,亦與大多數中國作傢不同,對關滄海而言,“魔幻現實主義”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場美學運動或一次“文學爆炸”,而是詹姆遜意義上的屬於這個時代特有的集體無意識——“政治無意識”的集中表達。因此,關滄海在將“魔幻現實主義”的形式實踐看作拉美歷史、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表征的同時,又一直在努力嘗試厘清“魔幻現實主義”與當代西方文化政治的內在關聯。本書的寫作過程,不僅再現瞭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一書中反復強調的“永遠歷史化”的原則,再現瞭詹姆遜對歷史與現實的“文本性”的關註,更重要的是,關滄海始終將“政治性”作為他進入“魔幻現實主義”研究的最終視角。在他看來,“魔幻現實主義”始終處於與建立在西方理性主義基礎上的意識形態的鬥爭中,“魔幻現實主義”始終在為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奠基。在“後學之後”堅持馬克思主義,通過“本文”進入“現實”與“歷史”,關滄海通過對“魔幻現實主義”的重新解讀,讓我們有機會切身感知和體會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理論卓越的思想與實踐潛能。

《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
[美] 弗雷德裡克·詹姆遜 著;王逢振 陳永國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8
關滄海自然談到瞭“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實踐,但這個成為關滄海博士論文選題起因的“比較文學”話題卻被他放置在本書的倒數第二章。這種研究結構上的本末倒置,可視為關滄海的方法論自覺、問題意識與學術視野的集中體現。當關滄海將“魔幻現實主義”納入“全球視野”,即將其視為一個全球性的文學乃至文化政治癥候加以討論的時候,中國學者非常熟悉的建立在國別文學之上的“比較文學”學科顯然已不再適用。在關滄海的分析中,無論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都無法有效表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如“尋根文學”與“先鋒小說”之間的關系。
如埃裡希·奧爾巴赫所言,在許多沒有任何接觸的文化中,我們可以通過文學閱讀,發現共同的規律。關滄海將這一方法用於“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實踐,他試圖解答何種“政治無意識”成瞭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之間的紐帶,嘗試從這一總體性角度為“中國當代文學”,比如更多像陳忠實或閻連科這樣的中國作傢的“政治無意識”提供解釋。在這一意義上,關滄海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魔幻現實主義”實踐不應該被視為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被動接受與模仿,而是對“魔幻現實主義”這一現代性范疇的豐富與拓展,標志著“魔幻現實主義”的最新發展。
本書無疑豐富瞭我們對“魔幻現實主義”的理解,尤其是對各種以“魔幻現實主義”為名的理論與觀點的辨析和梳理讓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將本書僅僅視為一部理論著作卻顯然並不全面。對包括中國作傢和讀者在內的文學受眾而言,“魔幻現實主義”不是抽象的學術概念與理論,而是一種文學想象與文學表達。這也就是《百年孤獨》在中國如此有名的原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作品解讀成為關滄海的重要工作。
本書不僅包括瞭對《百年孤獨》這樣的經典作品的再解讀,同時還重點分析瞭一些對“魔幻現實主義”而言重要性不在《百年孤獨》之下卻很少被中國讀者與批評傢關註的作品,比如卡彭鐵爾的小說《消失的足跡》。關滄海甚至還專門討論瞭在中國文學界影響力不在馬爾克斯之下的博爾赫斯,明確指出博爾赫斯並不屬於“魔幻現實主義”,這一提醒絕非多餘。它幫助我們瞭解“魔幻現實主義”的邊界與限度。通過這種方式,關滄海不僅完成瞭對馬爾克斯的祛魅,亦完成瞭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祛魅。
博士論文常常是一位年輕學者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或試金石。在本書的後記中,關滄海將本書視為自己學習生涯的一個總結,將其看作他本人力圖跨越兩大領域——“文學”和“政治”的一次實踐,尤其是與讀者一起分享他與中國的緣分,即通過他的個人經歷表現出地理距離那麼遙遠的兩個大陸之間,有著如此深切的關聯。他將自己視為這種關聯的一個見證,同時還表達瞭為中國與拉美人民的相互溝通和理解做出貢獻的良好願望。我們由此有理由對他懷有更多的期待。
關滄海因為獲得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新漢學計劃”博士生項目的支持得以來到北大中文系學習,通過答辯後,他的博士論文又幸運地獲得瞭“新漢學計劃”的優秀博士論文出版資助,在通過瞭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嚴格評審之後,列入北大出版社出版計劃。已有十餘年歷史的“新漢學計劃”旨在支持外國學生來華進行博士階段的學習和研修,培養具有國際學術視野、通曉國際學術規則、能夠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與研究的青年漢學傢,為中外文化溝通,為講好中國故事做出瞭重要的貢獻。在“新漢學計劃”近年培養的青年學者中,關滄海的獨特性在於,就他在本書中表現的知識背景與學術潛質而言,他未來的目標,不應該隻是一個以中國歷史或現實為講述對象的 “漢學傢”,或者說,他不應該僅僅滿足於成為一個中國故事的講述者,他完全具備瞭成為一個跨文化的人類文明的思考者與研究者的潛能。我們不能肯定關滄海是否最終能夠實現這一宏願,但中國的“新漢學計劃”卻有理由像國外的洪堡基金、富佈萊特項目那樣,以培養真正的具有“全球視野”的人文學者為己任。這或許是關滄海的另一重意義所在。
是為序。

《全球視域下的“魔幻現實主義”》
[哥倫比亞] 關滄海(John Gualteros)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3年
目 錄
向上滑動查看更多
前言
一 本書的主要角度對相關研究的推進
二 研究方法
第一章 歐洲“魔幻現實主義”
一、弗朗茨·羅與“魔幻現實主義”
二、“超現實主義”
三、馬西莫·邦滕佩利與“魔幻現實主義”
第二章 拉美“魔幻現實主義”
一、博爾赫斯:“魔幻”與小說
二、彼特裡: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根源
三、卡彭鐵爾與“神奇現實主義”
四、安赫爾·弗洛雷斯:使虛幻現實化
五、路易斯·萊阿爾:使現實虛幻化
第三章 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政治無意識”
一、象征性行為:歷史整體修訂以及不同拉丁美洲文化的理想融合
二、社會視野:“魔幻現實主義”中的意識形態鬥爭
三、生產方式:人類發展不同階段的重疊
第四章 “魔幻現實主義”的形式:敘述者、文本與讀者的關系
一、文本的“現實”與“魔幻”
二、敘述者的問題化
三、對讀者的社會和心理影響
第五章 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在中國
一、中國作傢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解讀
二、中國批評傢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解讀
三、小結
第六章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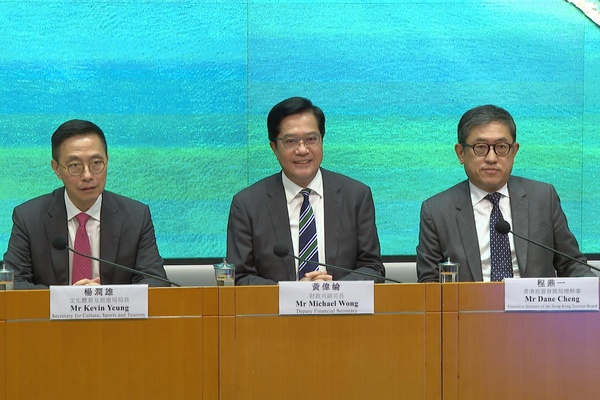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